原创 北京大学学报
作者简介
田晓菲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3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从白门到紫陌:“地”在文化史中的隐显与浮沉
摘 要:
从南朝到唐代,建康/金陵和“江南”在话语层次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建构过程。南朝诗歌通过对“金陵帝王州”的想象和对“江南佳丽地”的再现,逐渐把建康从偏安王朝的行政总部改变为帝国名都,经过唐代诗人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把建康写入文化版图,而“江南”的文化意义也逐渐和它的地理意义出现张力,甚至颠覆了它的地理意义。最后,通过对“紫陌”作出的词语考古,展示一个在南北朝时期曾真实存在的地点如何从文化版图上消失,从反面说明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和地理历史、社会历史的不同,以及它对文本特别是某些文本和某些体裁的依赖。
关键词:建康/金陵;东晋南朝;江南;词语考古;文化史阅 读 导 引
一、长安与建康:诗人的幻觉
二、名字与身份、砖瓦与文字:从行政总部到帝国之都
三、“江南佳丽地”:“金陵怀古”的前后
四、“紫陌”:镜子反面的图像
很多地方只有过去,没有历史;只有居民,没有故事。有些地方,则有太多的历史和故事,比如南京。在这篇文章里,我希望检视一下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当然要从六朝讲起,因为南京是六朝古都,但是,都城的身份实际上仅仅是故事的一个因素,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因素,但绝不是全部,因为不是说一个城市只因做过某王朝和某政权的都城就必然有故事。最后,本文将提供一个反面的事例,通过对“紫陌”一词的词语考古,看看一个真实存在的地点是怎么从文化版图上逐渐消失的。归根结底,本文旨在展示,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不仅不同于它的地理历史,也不同于它的社会历史;对于文化历史来说,文本往往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有些文本的重要性,超过了另外一些文本的重要性。
一、长安与建康:诗人的幻觉
让我用南朝诗人庾信(513—581)的一首诗开始。被杜甫誉为“老更成”的诗人庾信,有着惊人的笔力:南京从一个仅仅有居民、有过去的城市,到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帝都,整个东晋南朝三百年的历史,就包含在这首二十个字的绝句里:
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暝浦,应有落帆还。
这首绝句题为《望渭水》。渭水是长安的河流。庾信生长在南方,出仕于萧梁王朝。6世纪中叶,江南爆发侯景之乱,梁元帝派庾信出使定都于长安的西魏,庾信被扣留不遣,很快梁朝灭亡,西魏也被北周代替,庾信终其后半生都作为羁旅之臣滞留在长安,再也不曾返回江南。
在这首诗里,诗人眼望渭水,出现幻觉,觉得渭水边上的树好像是新亭旁边的树,渭水边的沙滩好像是龙尾湾的沙滩。新亭和龙尾湾都是南方地名,更确切地说是南朝首都建康的地名,在长江边上。诗人是说,虽然身在长安,但是因为对建康的怀恋,眼中所见都是建康景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新亭的指称。庾信同时代的读者,都会知道这个关于新亭的有名的故事,这是《世说新语》“言语”篇里的版本: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过江”的一代人,是西晋首都洛阳陷落后南渡长江、建立东晋的难民加移民。他们在长江边上的新亭观看江山风景,想到洛阳四面青山、中有洛水的景色,痛感此水非彼水、此山非彼山,于是悲哀流泪。现在,三百年之后,庾信同样也是过江者,但他却是北渡而非南渡,也并没有“归国”之感,反而在长安和渭水之畔,思念建康和长江。庾信在北方的诗,常把南朝故国称之为“楚”。王导曾经责备东晋的北方中原人士作楚囚相对,如今庾信却堪称真正的楚囚。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讽。
龙尾湾是诗中的第二个地名,同样引人瞩目,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位于建康西南的新亭非常著名,它是长江上风景优美的名胜地,也是出入建康的要地,整个南朝时期,它既是公宴与祖饯的所在,也有驻军的堡垒。和新亭不同,龙尾湾是个只有建康本地人可能才会知道的小地方。如果翻检《南史》,我们可以看到“新亭”出现七十多次,龙尾湾却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南朝文字唯一提到这一地名、而且把龙尾湾和新亭联系在一切的,是一首乐府歌曲《白浮鸠》:
石头龙尾湾,新亭送客渚。酤酒不取钱,郎能饮几许?
我们不知道庾信是不是知道这支歌,但是我们知道《望渭水》的下半,一定是对前辈诗人何逊(约518卒)的致敬与回应。何逊有一首诗题为《宿南洲浦》:
幽栖多暇豫,从役知辛苦。解缆及朝风,落帆依暝浦。违乡已信次,江月初三五。沉沉夜看流,渊渊朝听鼓。霜洲渡旅雁,朔飙吹宿莽。夜泪坐淫淫,是夕偏怀土。
庾信的“犹言吟暝浦,应有落帆还”就是何逊“落帆依暝浦”的转写:诗人继续他的幻想,想象在天色渐晚的河流上,落下船帆,回归故乡。如果诗歌典故构成一种歇后语,那么庾信诗隐去的后文,就是何逊诗的最后一句:“是夕偏怀土。”
庾信的诗所反映的,是因感情的纠结而导致感官的迷乱。这样把心理的变化“翻译”成物理变化的做法并不少见,南朝诗就有因为心思的烦乱而导致“看朱成碧”的说法。庾信诗的特别之处在于,在南朝的诗歌里,我们时时处处可见诗人用周、汉、西晋一路下来的长安和洛阳来代称建康,用长安、洛阳的地名、宫殿名来比附建康地名和宫殿名,但是庾信的诗,却破天荒次用南朝地名来比附北方周汉旧都的长安。换句话说,每次我们说“甲很像乙”,我们都是在把乙作为位的、甲是第二位的,乙是甲的参照系,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说长安像建康,根本就是违背了此前的诗歌传统和思考方式的。
但是,作为被扣留在北方的、故国沦陷的南朝人,庾信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处境,因此,他必须用一反常态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全新处境给他带来的震惊与创伤。与此同时,庾信的诗还反映出了建康的变化:从东晋南渡初始面对内忧外患的仓惶郁闷,到繁荣、蓬勃、自信的萧梁王朝,建康的地位和身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也是秦汉以来中原政治文化中心视之为蛮荒边地的江南被建造为佳丽地的过程。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名字与身份、砖瓦与文字:从行政总部到帝国之都
南京最早的名字是金陵,得名起始据说是周显王的时候,楚国灭越(前333),尽得吴故地,因为人说此地有王气,于是埋金(不是金子而是金属,可能是铜铁之类)以镇之,故名曰金陵;到秦始皇的时候又有望气的人说:“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于是秦始皇东游以厌镇之,并把金陵的名字改为秣陵。公元211年,孙权把治所迁移到秣陵,次年改名为建业,显然有建立王业的意思。到了280年晋武帝平吴,重新改为秣陵,到282年,太康三年,分秣陵北为建邺,但很有意味地把“业”字改为“邺”字。313年,晋愍帝司马邺登基为帝,为避司马邺的名讳而改为建康。至此我们看到:建康作为一个地方,在文本传统里已经有了将近六百年的存在历史,而且在孙权称帝后首次成为王朝首都,但是在文化史上,它却基本是缺席的。吴国灭亡后,虽然有著名作家陆机为它作《辨亡论》,但是对建业的陷落却无人在文字中表示哀悼。吴国的建业,还没有乌衣巷,没有玄武湖,虽然长江中的沙洲一定从来都有很多白鹭盘旋飞舞,但没有人知道什么“白鹭洲”,更没有什么鸡鸣埭,或者临春阁。换句话说,吴国的建业乃是吴国统治江南的行政中心而已,但是它作为一座城池,却基本上默默无闻。
317年,晋元帝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世说新语》“言语”篇里有一则有名的故事:有人批评王导“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和桓温营建的姑孰“街衢平直”相比稍逊一筹。王导的孙子王珣为王导辩护说:“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王珣颇有口辩,他的回答固然巧妙,对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一点却是它所反映的时人对江南的认识:秦汉以来,江南一直被北方人士视为荒蛮的边缘地带,东晋政权的第二、第三代中土移民已经对回返中原感到顾虑重重,但是他们对江南的印象却还是可以用传统的轻蔑判断来进行概括:“江左地促,不如中国。”
元帝始镇江东,东晋政府作为流亡政府,“公私窘罄”,就连一口猪都被视为“珍膳”。公元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东晋王朝都在忙于镇压内部叛乱、击退北方威胁,首都的建设并非首要关怀。尽东晋一朝,唯一的大规模城市建设是由谢安(320—385)在378年执行的。谢安与王彪之(305—377),作为著名的王谢家族的翘楚与代表共同执掌朝政,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两人协商一致。在修建宫室的问题上,二人态度迥异。王彪之虽然也承认皇宫“方之汉魏,诚为俭狭”,但认为可以凑合下去,因为“强寇未殄,正是休兵养士之时,何可大兴功力、劳扰百姓邪!”谢安回应说:“宫室不壮,后世谓人无能。”这一回答显得十分微弱无力,只给了王彪之一个说教的机会:“任天下事,当保国宁家,朝政惟允,岂以修屋宇为能邪!”这种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使谢安无言以对,因此大规模营建直到王彪之故世后才得以进行。王彪之与谢安在这一议题上的意见分歧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王彪之代表的是儒家强调节制俭朴、与民休息的熟悉论调,然而谢安展现的却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视野,也就是说,意识到舆服建筑这些眼目可及的物质标志在代表国体和王朝合法性方面的重要,它们是王者与帝国尊严的具体可见的体现。只不过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里,勤俭建国、休息百姓的主张可以轻易找到大量理论来支持,“大修宫室”的理念却缺乏话语资源(萧何对汉高祖的回答是少数例外,见下文)。因此,谢安无法引经据典,对王彪之的抵制作出有效的反驳。
基于种种现实原因——财力、物力、人力有限,内忧外患频仍,权臣往往有自为之心,和政治紧迫性的缺乏——在东晋一朝对王朝合法性的建构过程中,都城与宫室的建设并不是朝廷的当务之急。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这样的形势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谢安的营造方案或可谓此一转变的早期征兆。
对建康的构筑产生最早和最重要影响的是宋文帝(407—453;424—453在位)。宋文帝的父亲,是取代了东晋的刘宋王朝的创建者宋武帝刘裕(363—422;420—422在位)。从东晋最后两个皇帝开始算起,宋文帝是江南半个世纪以来位成年登基并且长期执政、掌握实权的皇帝。这位年轻君王即位后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强大的贵族精英集团,二是北朝劲敌的崛起。北魏太武帝拓拔焘(408—452;423—452在位)于公元439年统一了北土,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它终结了北方逾百年的强权纷争,正式开启了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一对南朝构成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一方面意味着之间必须维持势力的均衡,一方面与皇权正统性密切相关。为了与统治了传统华夏疆域的有力对手抗衡,也为了对抗本土的世家大族菁英,宋文帝都需要“展演王权”,展示和表演他的王朝统治的正当合法性,激发臣民对他个人至高权威的信心。
必须说明的是:“王权”(kingship)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帝王的权力,而是意味着君主的身份、地位和尊严。它是一个想象的社会建构。君主在本质上和任何一个普通人并无区别,他凭借他的权威行使权力,而他的权威事实上是由他的臣下、也就是一个社会菁英阶层赋予他的,他的权利基于他人对其君王身份和地位的认知与认同。权力既然来自他人的主观感受和认知,就必须具有可见度,必须通过展现了社会等级区别的象征性标志显示出来:服饰、车舆、居处,无不起到关键作用。居处包括宫殿,也包括作为帝国心脏的首都。在这方面,宫室尚简朴的传统政治道德话语并不能满足和解释王权建构实际的运作和需要。
公元5世纪30及40年代,宋文帝在位期间,建康在南朝的营造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建筑项目包括建造北苑,后来改名乐游苑,于覆舟山一带大起楼台;438年,建造东宫,使之成为“制度严丽”的居所;446年,扩展与翻新华林园,修建玄武湖。此外,还有443年皇城的城门建设和448年建康城的城门建设。
除了砖石瓦当的营造之外,文字的经营也至关重要,甚至比物质的建筑更重要。在宋文帝的引领下,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对建康城首次大规模进行的文本建构。公元446年,宋文帝修筑了一座人工的景阳山,景阳山顶有一座景阳楼。宋文帝作有《登景阳楼诗》,尚有八联传世,下面摘选数句:
崇堂临万雉,层楼跨九成。瑶轩笼翠幌,组幕翳云屏。……极望周天险,留察浃神京。……士女炫街里,轩冕曜都城。万轸杨金镳,千轴树兰旌。
诗句首先描述了楼台的高度以及它与壮丽京城的相对关系,次及高楼的深度,如何掩藏于重重帷幌屏风之后,幽深难测。上引第三联,强调了君王视野的开阔和包容。最后四句写都城人口稠密,舟车往来不绝。建康作为帝国中心,是水陆交通运输和信息传递的中转枢纽,而君王从高耸的景阳楼上眺望到的风景,从近在眼前的细节局部一直延伸至帝国的四面八方。这里有对江南帝国疆土感到的骄傲,有对建康城作为帝国心脏的赞美,更展示了君王视线普及天下、无所不包的容量。数十年后,南齐(479—502)法制规定:“诸王邸不得起楼临鸟瞰宫掖。”正是因为深深明了在观望和知识中所蕴含体现的权力运作。
谈到文帝对建康城大力进行的文本建设,就不能不提到文帝最欣赏倚仗的宫廷诗人颜延之(384—456)。颜延之是所谓“元嘉三大家”之一,相比其他二位“大家”谢灵运和鲍照,颜延之在后代很少为人注意,但是,他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中、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他的重要性在于他想象与建构帝国的能力,也就是钟嵘(518年卒)所指出的“经纶文雅才”。在一篇题为《南朝宫廷诗歌里的王权再现与帝国想象》的长文中,我曾详细论述宋文帝对建康的缔造和颜延之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里仅举一个例子。
公元449年,颜延之陪伴宋文帝前往京口,写下《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京口位于建康以东、长江南岸,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同时,京口也是刘宋皇帝的故乡,宋文帝及其父宋武帝刘裕都是在京口出生的。宋文帝在位期间,曾两次亲临京口,一次是在427年,另一次则是在449年。第二次巡幸长达三个月之久,期间在京口颁布诏令,以“北京”称呼京口,以为“皇基旧乡,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迁数千家以充实之。蒜山是京口一座俯瞰长江的平顶小丘,上面野蒜丛生,因而得名。作为山丘来说,蒜山相当低矮平凡,但是,颜延之对它的文字再现,却把我们带到一个表现王权与帝国的高峰。诗的联极有气势:
元天高北列,日观临东溟。
“元天”是一座神话中的山,据《文选》李善注,其山之高,“四见列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特别强调这座山位于北方。天体的意象在下一句“日观”的名字中继续出现。日观也是泰山峰名,由此可观看日出也可俯眺东海。从天到海,从仰观到俯视,诗的开头可谓气象万千。
入河起阳峡,践华因削成。
第二联围绕两个北方地景——黄河与华山——展开,其潜在结构是贾谊的《过秦论》这一文本:“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按照贾谊的说法,黄河、华山是维护秦朝首都咸阳的天然屏障。如此一来,诗人在开头四句展现出了一幅北方的壮阔风景。然而下面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岩险去汉宇,衿卫徙吴京。流池自化造,山关固神营。
“岩险”“衿卫”二词都出现于东汉作家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值得注意的是,以建康为首都的吴国,和大汉帝国原本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借由“吴京”与“汉宇”的对仗,诗人把“吴”和“汉”放在平行对应的位置,“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而且,当诗人宣称北方陡峭的天险已离开汉土、徙置建康时,他是在一手改天换地,把北境的山川险阻移到了南方。换句话说,这里的“岩险”与“衿卫”,指的是长江与蒜山这些环绕南朝帝都的天然屏障。作者用“造”与“营”来形容造物者对于地势地形的塑造经营,这两个强调人力构筑的动词,正好巧妙地形容诗人自己如何以天神般的巨力移山倒海,将异域地景挪移至南方。这是只有在文字里、只有在善于运用文字的人手里才能表演的魔术。
建康的营造在宋文帝之子宋孝武帝(在位)治下继续进行。相对文帝,宋孝武帝无论在砖石建筑和文字营造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454年建造正光殿与孔庙;459年于玄武湖北岸创建上林苑;461年修建礼殿,开立两条驰道;462年修筑凌室,新建城门大航门。孝武帝好文章,文集多达三十卷,七世纪初尚有二十五卷传世。刘宋之后的萧齐王朝,其创始人齐高帝萧道成(479—482在位)在建康的营造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元480年正旦元会,有人以韵语上言:“白门三重关,竹篱穿不完。”“白门”是首都建康城南宣阳门的俗称。当时,建康城没有一座真正的砖砌城墙,围绕城市的是木栅竹篱,这两句韵语是说:白门尽可以重重上锁,但是围绕建康城的竹篱残缺不完,不足以保证城市安全。这两句包含讽刺的韵语非常触动齐高帝,他于是下令修筑城墙。此前,齐高帝曾打算用刘宋某宫殿拆除后的材料建造宣阳门,被大臣用“勤俭节约”的理由阻止,如今他们又对修筑城墙表达反对意见,但这一次高帝没有再屈服,他引用被南齐萧氏皇室视为祖先的汉朝开国大臣萧何的话,说:“吾欲令后世无以加也。”当年萧何因大修未央宫而惹怒汉高祖,针对高祖的批评回答说:“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萧何是历史上少数为大造宫室进行辩护的人,虽然如此,他的辩护词也还是把不应陷后代子孙于奢侈作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论点。
萧齐时代建康城墙的修筑,是建康城市史上重要的新篇章。高帝之继任者齐武帝(482—493在位)在永明年间也有很多修缮营造,如青溪旧宫、商飙馆、新林苑、兴光楼,其中兴光楼因涂以青漆而被京城百姓称为“青楼”。有感于砖木建筑的无常,武帝在去世前留下的遗嘱中,曾特别针对他在位期间修造的三座宫殿提出:“夫贵有天下,富兼四海,宴处寝息,不容乃陋,谓此(按指凤华殿、寿昌殿、耀灵殿)为奢俭之中,慎勿坏去。”永明年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专门于491年派将作大匠蒋少游(501年卒)出使南朝,学习建康皇宫的设计。南北朝之间的较量不仅发生在军事的层次,也发生在话语和象征的层次。当时,齐臣崔元祖上书齐武帝,要求扣留蒋少游,认为“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但齐武帝否決了这项提议,其后“少游果图画而归”。
文字的营造也在下一代诗人手中继续。齐武帝深知立言之不朽,因此常在朝廷宴饮中命朝臣撰写诗篇。《隋书·经籍志》载有《齐宴会诗》十七卷,以及《青溪诗》三十卷,注云:“齐宴会作。”青溪宫是武帝出生之所,永明二年(484),武帝下诏,表示将克日游幸,同年八月丙午,“幸旧宫小会,设金石乐,在位者赋诗。”这些诗想必收入《青溪诗》中。萧齐诸王也常令从臣赋诗。这些应教之作,虽然在创作场合与直接目的方面,和颜延之在正式场合对王权帝国浓墨重彩的有意缔造不尽相同,但它们在客观上起到的作用,无不是在巩固加强建康作为辉煌帝都的形象。
周、秦、汉和西晋王朝的首都,无不依傍名山。随着建康逐渐成为南方帝国的“图腾式前厅”,城北的钟山也逐渐被写入文化版图。深受颜延之影响的宫廷诗人沈约(441—513)在5世纪80至90年代之交写过一组诗,题为《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五首》。这组诗实则是分为五节的有机整体,首作为组诗的部分,阐明了钟山的象征意义:
灵山纪地德,地险资岳灵。终南表秦观,少室迩王城。翠凤翔淮海,衿带绕神坰。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
首联以“灵”起以“灵”终,“山”“岳”是同义词;“地德”“地险”中“地”重复两次,造成一种回环往复的回文效果,并以“德”与“险”的对应分別暗示王者的道德资本与军事力量。第二联,上句谈长安以南的终南山,秦始皇曾在此山设立戍楼,而下句的少室山则是嵩山的一部分,邻近东汉、西晋的首都洛阳。终南山就在长安旁边,但是把终南山与秦朝而不是和汉朝联系起来,创造出时间上的变化(自秦至汉)和空间上从西到东的移动感(长安至洛阳)。第三联中,我们再次看到时间与空间的进程:凤凰翱翔南土的意象,是南方帝国建立的象征;而“衿带”一词,让我们想起颜延之诗中的“岩险去汉宇,衿卫徙吴京”。最后,在作出一系列铺垫之后,钟山终于以青翠挺拔之姿出现。
就在蒋少游学习和图画建康宫殿设计的前一年,沈约的好友谢朓(464—499)撰写了对建康和江南的著名礼赞: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迆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这首《入朝曲》是十首《鼓吹曲》的其中一首,为谢朓奉齐随王萧子隆(474—494)之命所作,就像上面沈约的诗一样,也被收入萧统(501—531)主编的影响深远的《文选》。鼓吹曲为仪仗队在马上演奏的军乐,是诸王与建立功勋的贵臣才可以享受到的殊荣。《入朝曲》描述了想象中王子和随员从藩镇入京朝觐的直线性行进,从王子从远处看到首都的建筑开始,沿着两边夹着御沟的笔直的驰道一直前行,直到最后进入皇宫。
就像中国古代的建筑一样,中国古典诗歌也喜欢回收利用诗的建筑材料。齐高帝曾想用刘宋故宫的材料重建宣阳门,而谢朓这首诗的联源于曹植描写长安的诗句:“壮哉帝王居,佳丽殊百城。”然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曹诗里,壮观和佳丽都是形容长安这一座城池的,但在谢朓诗中,他却先以大远景镜头描绘整个的江南:不再是充满瘴气的蛮荒之地,而是一块乐土;然后,才把镜头对准建康,以“帝王州”的来点出建康作为帝国心脏、政治中心的身份。“佳丽地”和“帝王州”相对,一是地理空间,一是政治疆域;一则强调魅力,一则强调威权。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用建康最早的名字“金陵”来称呼这座城市,似乎在有意回应在千余年前金陵有“王气”的预言。没有其他的诗句能像这两句诗那样明确展现建康城在这个时代的新意义。至此,经过半个多世纪不懈的建设,南朝君臣已经把建康从一个政府的行政总部创造成了一座帝都。
三、“江南佳丽地”:“金陵怀古”的前后
与“金陵帝王州”相互表里的是“江南”的文化建构。在《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一书中,我讨论了“‘南’‘北’观念的文化建构”,本节则集中讨论“江南”一词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冲突张力,以及“江南”与建康的营造构成相互依附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江南一词的本义是“长江以南”,因此包含的区域从原则上说涵盖整个南中国。在秦汉时期,南方虽然归属于帝国的行政疆域,但是从文化上说,相对于北方名城大都长安和洛阳,却属于边缘。在早期对于南方的想象中,南方是一块湿热瘴毒、巫风弥漫的蛮荒之土。南方很大一片地区处于古老的、以湖北湖南为中心区域的楚国境内,“江南”也因此常和楚文化联系在一起。公元6、7世纪之交,隋朝统一南北之后,北人孙万寿(约581—601年在世)因微过被配戍江南,写下“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的悲怨之句,这种故意与“江南佳丽地”对立的诗句由来有自,属于屈原、贾谊一路相通的传统;但是,我们看到,江南的这种原始形象被南朝君臣所致力经营的新江南有效地复杂化,被逐渐局限于南方的部分地区也就是古老的楚地。如果说在南朝时期,“江南”一词还可以包括对潇湘地区的想象,那么,到中晚唐时期,对“江南”的联想逐渐地缩小地理范围,变得与三吴地区也即今天的江苏、浙江特别是南京、扬州、苏州、杭州这一系列城市紧密相关。扬州的例子非常能说明江南一词的文化意义对其地理意义的超越和代替,因为严格地说,扬州地处“江北”,不在“江南”,但是,它却绝对属于“文化江南”的一部分。这个“文化江南”形成的过程,是一个缓慢、复杂和长期的过程,而它最早的开始,事实上与建康作为帝都与公元5世纪和6世纪前半“南方帝国”的兴起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提到江南的新形象,我们不能不提到南朝的歌曲:它们有些来自城市娱乐场所,有些则出自宫廷乐师、贵族、王子甚至皇帝之手,作为宫廷音乐的一部分被保存下来(陈朝僧人智匠编撰的《古今乐录》,通过11世纪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得以传世,是这些曲调歌词最重要的来源)。一首系于梁武帝萧衍(464—549,502—549在位)名下的《子夜夏歌》,把江南表现为色彩艳丽、充满的国土:
江南莲花开,红光覆碧水。色同心复同,藕异心无异。
在这些艳歌中,一方面作词者采用了江南乐歌常用的双关语表现情爱,另一方面,情爱的语言本身就构成了佛教经典中色/空概念结构的一部分。莲花是色欲之花(莲/怜,藕/偶),也是净土之花,完美地体现了肉身与超越的吊诡结合。此处莲花特地和“江南”联系在一起,它的背景音乐是一首古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莲是可食的植物,从种子、根茎,到花与叶,无不可入食或者入药,因此,采莲是中国很多地方都进行的活动,并不限于江南;但是,通过这些文本意象和它们在后代的不断引用,“采莲”在通俗想象中永远成为“江南”的象征符号。
需要指出的是,在南朝诗歌中,“江南”一词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地理伸缩性,还没有像在后代那样专指长江下游的吴地。齐、梁时代的贵族诗人柳恽(465—517)写过一首《江南曲》,诗中提到洞庭、潇湘,显然涵括了楚国故地:
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久不返,春华复应晚。不道新知乐,且言行路远。
这首诗描写一个旅客在归途上遇到故人,这位故人在外漫游时结下新欢,宁愿在潇湘一带淹留不返,忽略归客委婉的暗示(“家中有人在等你呢,否则春华将晚、思妇韶华将逝”)。最后两句,或可视为他对归客的嘱咐:回乡后,切莫说我流连于新知,只说路途遥远耽误了归程。
诗简单而优美,但是,诗人在朴素的语言里,用湘水、洞庭、汀洲、白苹这些因素含蓄地呼应《楚辞》“湘夫人”里对意中人充满思念渴望的叙事,如此一来,在变心的游子和家中思妇这个普通的故事之下,我们听到了人生脆弱、爱而不得的永恒感喟,无论是单相思的情人还是羁旅之臣,对此都有同样强烈的体会,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柳恽的诗在后代诗歌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以至于他自己成为一首诗中的角色:
汀洲白苹草,柳恽乘马归。江头楂树香,岸上蝴蝶飞。酒杯箬叶露,玉轸蜀桐虚。朱楼通水陌,沙暖一双鱼。
这是李贺(790—816)的《追和柳恽》。这恐怕是诗歌传统里首次把一个已逝的诗人拿来作为诗中人物的诗。在这首诗里,柳恽自己即是洞庭归客。诗人的视线,从第二联室外的春暖花开,转向第三联室内饮酒鼓琴、其乐融融的情境,最后,含蓄而知趣地把摄影镜头从朱楼中的情人转向朱楼外的水陌,画面拉近到被春天阳光晒得暖洋洋的沙上的一双鱼儿。这既是杜甫“沙暖睡鸳鸯”的变形,也隐含了“鱼戏莲叶”之后满足的倦怠。诗并无深意,却是意象和语言精心出来的和谐纹理,具备了色、香、音声、味道、接触这五种感官的反应。这首诗,把漂泊漫游者带回他的故乡,在空间上把重心从潇湘洞庭的楚地转移到吴地,在时间上令历史人物进入到圆满静止的状态。唐代皇室子孙的李贺,为南朝的贵公子在诗中安排了一个美满的结局。
李贺的诗具有代表性:中晚唐诗人作家——包括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包括牛僧孺、张读、沈亚之、李玫等等——对南朝深感兴趣,在一大批诗歌和传奇作品中,他们把南朝浪漫化、小说化,正像李贺此诗所做的那样。这些塑造了南朝形象的诗文往往围绕着建康Ϧ金陵或者其他三吴之地展开,也帮助促成了“江南”形象的建造。如果我们追根溯源,那么我们必须回到8世纪也就是盛唐时代“诗歌中的金陵”的生成,回到“位真正的金陵诗人”李白(701—762):对此学者已有专门论述,兹不复赘。这里,我们仅需强调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些“金陵怀古”诗作中,和金陵联系得最紧密的,并不是周、秦、汉、三国、西晋,即使金陵作为一个城市在彼时已经存在;而是东晋南朝的人物、事件、景观。
杜牧(803—852)有一首著名的《江南春绝句》,诗题回应了柳恽的“日落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诗的句,令人想到谢朓《入朝曲》开始对广大江南的远景镜头摄影,而色彩明艳、莺歌燕舞的江南也仍然如谢诗中歌颂的那样佳丽。但是,转入第二句,我们不再看到“帝王州”,相反,乡村城郭,处处酒旗招展,寻常百姓在这块土地上过着他们的生活,享受着他们的生活。第三、四句,非常具体的数字(“四百八十”),和不知究竟有多少的楼台,构成了极有兴味的对比。和谢诗中视线的直线进程不同,杜诗中诗人的视域被烟雨遮挡,让读者永远无法知道:最后一句诗到底是一个惊叹句呢——换句话说,就是:“江南真有好多的楼台啊!”——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它又可能有几个答案?也许是“多到数不清”,也许是“一座也没有了”,因为诗人强调那些寺庙是“南朝”的寺庙,而佛寺的存在,正是为了提醒人们“一切皆空”的佛教教义。
春回大地,诗人听到莺啼,看到大自然红绿相间的色彩,感受到吹拂酒旗的春风,然而却无法摆脱历史的幻影:其实,千里江南,无数寺庙,何必非得是“南朝”的寺庙?但是对9世纪的诗人来说,它们必是“南朝”的寺庙,哪怕他无法真正看见它们。从小谢写下他的名作到杜牧的时代,又是三百年过去了,在经过了南朝、盛唐与中唐很多文本的经营建设之后,当杜牧再次面对这块“佳丽地”,他已经无法不感受到“南朝”。
就像“金陵”成为“怀古”的对象,“江南”也成为“失落”的象征。即使不和历史记忆与失去的帝国联系在一起,它也仍然和个人的记忆与不可复得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白居易(772—846)的三首《忆江南》深入人心,脍炙人口: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首就好比小杜的《江南春》那样充满艳丽热情的色彩,但是因为镶嵌在怀旧的框架中而带上一丝惆怅,好似有意用棕褐色调制造出的老照片效果。白居易的诗,既抒写了诗人自己对江南的怀念,也帮助加强了江南作为失落、作为回忆的怅惘意象,更完成了江南的地理疆域逐渐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缩小为吴地甚至苏州、杭州等几座城市的过程。这些诗直到今天仍然被收录进小学课本,使多少孩子在没有见到江南之前,就已经懂得回忆江南了。
四、“紫陌”:镜子反面的图像
最后,让我们用一个反例,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在6世纪,萧梁作家继续对王朝形象的营造,但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典范。如果说刘宋萧齐两朝总是以上古三代与秦汉作为主要的参考框架,那么有梁一代则经常以三国时代的曹魏宫廷作为范式。萧梁的宫廷桂冠诗人刘孝绰(481—539)有一首诗《春日从驾新亭应制》,特别能表现这一点。但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在于这首诗一开始时的一个令人困惑的细节:
旭日舆轮动,言追河曲游。纡余出紫陌,迤逦度青楼。
这几句是说车驾清晨启程,仿效曹丕的“河曲之游”,仪仗队连绵曲折出离紫陌、度过青楼。“青楼”本意是青漆粉刷的豪华楼舍,曹植名作《美女篇》有“青楼临大路”的诗句,前面也提到建康百姓也曾将齐武帝的兴光楼称为青楼,因此,刘孝绰的诗既用到三国时期的诗歌典故,也巧妙地指涉了当今景物。但是,如果我们都知道“青楼”的历史来源与当代指称,那么“紫陌”的词源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汉语大辞典》对“紫陌”的解释,是“京师郊野的道路”,并引用王粲(177—217)《羽猎赋》作为该词汇最早的出处。王粲的赋描写曹操在邺城近郊的一次狩猎,其中有云:“济漳浦而横阵,倚紫陌而并征。”翻开很多现代注本,会发现注释者一般都把“紫陌”解释为“京都郊野的道路”或是“郊野道路”。但是如果说我们明确知道青楼何以为青,那么紫陌何以会紫,却无人过问,至于“紫陌”何以成为京师郊野道路的代称,就更是不甚了了。更奇怪的是,在现存的中古文学作品中,从王粲之后,紫陌一词似乎销声匿迹,一直到6世纪上半叶,才再度出现于诗赋作品,而且集中出现在萧梁作家笔下。
从东汉末年到萧梁的三百年里,“紫陌”一词究竟怎么了?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用来代指“郊野道路”的文雅词汇,照理来说应当常常出现于文学书写中才对,但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不过,如果我们离开美文书写,把目光转向不同种类的文献,就会发现这个词汇不但并未消失,而且使用频繁,但根本不是什么郊野道路,而是邺城西北、漳水之东一条河的名字。据东晋陆翙《邺中记》,公元345年,后赵统治者石虎在紫陌河上建了一座浮桥,称为紫陌桥,并在近旁修筑了一座紫陌宫。《北齐书》等国史,东魏、北齐的出土墓志,都频频提到紫陌,如“神武令封隆之守邺,自出顿紫陌”“周师至紫陌桥”“高祖如京师,群官迎于紫陌”“葬于邺北紫陌之阳”,等等。这些资料显示,直到南北朝后期也就是6世纪末年,紫陌桥、紫陌河都一直是当代人频繁使用的地名。
继续追溯下去,我们会发现,紫陌所在之处,是著名的西门豹裁治巫婆的地方。郦道元《水经注》称:“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后来“淫祀虽断,地留‘祭陌’之称焉”。郦道元随即为我们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田融以为紫陌也。”田融是后燕时(384—407/409)人,著有《赵书》十卷,又称《二石记》或《赵石记》,郦道元对田融意见的引用显然来自这部佚失已久的《赵书》。郦道元并未具体说明田融为什么以为“祭陌”就是“紫陌”。我们也许可以推测说:祭(tsjejH)、紫(tsjeX)在中古时代发音相似,虽然一为去声而一为上声,但地名从口头流传进入文字书写时,很容易发生这样的转化。至此,紫陌虽然不能说完全真相大白,但在我们找到更多资料之前,或可暂时作出这样的结论:紫陌很可能原作祭陌,紫为祭之误。我们至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紫陌并不“紫”,也和“京师郊野道路”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紫陌一词之所以得到作家的青睐,和其色彩内涵密切相关。就现存文字材料来看,刘孝绰是继王粲之后位将“紫陌”用于美文写作和“青楼”映照的作者,其他萧梁及梁入陈之作者继其后尘,紫陌从此进入文学视野。如萧纲(503—551):“紫陌垂青柳,轻槐拂慧风。”萧绎(508—555):“朱城却棁,紫陌潜通。”徐陵(507—583):“铁市铜街,青楼紫陌。”江总(519—594):“轰轰紫陌上,蔼蔼红尘飞”,等等。南朝作家不仅摘取“紫”的颜色意涵创造色彩的对照,也利用“陌”字的“道路”含义来构筑巧妙的双关语,但他们显然深知“紫陌”本义为河流、桥梁、宫殿之名。如徐陵《报尹义尚书》:“白沟浼浼,春流已清;紫陌依依,长杨稍合。”白沟是曹操开凿的运河,白沟与紫陌对举,强调了它们作为地名尤其是河流名的共通性质。江总《陈宣帝哀策文》有“背紫陌而未远,隐黄山而不见”之句,则利用作为宫殿名的紫陌和黄山宫对举,造就精工的对仗。但是等我们到了唐朝,刘禹锡(777—842)著名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则显然是化用了上引江总《长安道》的成句。就连在唐代墓志铭中,对紫陌的用法也和南北朝墓志铭中的用法呈现出鲜明对比:在我们看到的四例中,紫陌都是装饰性的,没有一例把紫陌作为地名引用。究其原因,应是在北周灭北齐之后,北周权臣杨坚也即后来的隋文帝下令焚毁邺城,并将邺城居民南迁到四十五里外的河南安阳,齐都化为废墟,当地地名亦被人淡忘。紫陌逐渐成为一个纯文本的语汇,失去了它的地理意义。对后人来说,它从一条河流、一座桥梁、一座宫殿,变成了一条语焉不详的“京师郊野的道路”。
有些地景会因为文本而不断得到重建,然而紫陌的故事却让我们看到这种情形的反面: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如果没有文本的营造,特别是某一类体裁的文本和某些文本,则会被逐渐遗忘。在建康的情况里,从南朝和唐代,是诗歌这一体裁,因为容易记忆和流传的性质,对它的形象塑造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回顾庾信的绝句,短短二十个字,涵括了建康三百年的历史:从东晋移民刚刚到来时的“江左地促、不如中国”和“制置纡曲”,经过了宋、齐、梁三代的建造特别是文化的和话语的经营,建康终于从一个王国再到一个流亡政府的行政总部,变成了代表帝国门面的名都大邑;有了这种文化身份的转变,才有可能被诗人变成用以理解中原名城的坐标。在这首绝句中,反而是充满了历史遗迹的长安和渭水,在诗人眼里,不过是数丛“树”与一片“沙”而已。
建康是一座命运多舛的城市。隋文帝杨坚对毁灭敌国都城不遗余力:589年,在征服江南之后,他下令毁灭建康所有宫殿,把城市变成废墟:“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江南在文化史和政治史上都处于低调状态。但是,南朝诗歌经由唐代诗人的继承与发展,在文化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东晋南朝的故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命运也就完全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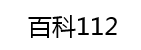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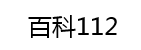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四川麻将血战到底输赢的规律”(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四川麻将血战到底输赢的规律”(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