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在新华路的一家咖啡馆与杨岚见面,是一个周一上午。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他来上海出席新书《琴人》的书店活动,举办新书分享会的计划早在今年3月就已经有了,但因疫情原因直到11月下旬才得以实现。采访当天上海依然是暖和到在室外疾走会微微出汗的天气,仿佛与春天仍相距不远。杨岚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一些,他戴着圆眼镜,清瘦,见人来了举手示意,打招呼时礼貌温和又没有过分热络,沉静笼在他的身上。
我们从他在分享会上弹奏的《流水》开始聊起——打开一个人的话匣子,最快的方式就是聊这个人熟悉擅长之物。对于习惯了西方或现代音乐的耳朵而言,西方音乐像是行进的,什么地方停顿、什么时候强弱都安排得严丝合缝;古琴曲则像流淌的河流,音符和琴弦震动产生的余韵都密密地缀在了一起,让人难以摸清韵律。
杨岚解释道,古琴其实也有自己的节奏,但相对其他乐器来说,它的自由节奏的确较多。事实上,古琴的曲谱不记节奏,演奏方式很大程度上靠师徒传承,在这一方面,北方琴家通常更严格,学生会完全模仿老师。但南方琴家对此的态度更随性,比如广陵派琴家在处理节奏问题时往往没有一个量化标准。杨岚自己早先喜爱北京古琴大家管平湖的演奏,但在摸索出自己的风格后发现,“我自己的演奏比较自由,不太受得了完完全全的模仿。”
“能自圆其说的自由发挥”或许是古琴音乐最独树一帜的特点。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古琴曲,哪怕是那些在琴史上赫赫有名的曲目也不例外。以《流水》为例,曲子的后半段中有一个炫技的桥段:演奏者右手手指快速拨弄各根琴弦,模拟出湍流激荡的水声。这一个被称为“七十二滚拂”的桥段其实是晚清琴家的创造。不同的时期,琴家都会对琴谱做出改动,或增加一段,或删掉一段,或改编某一段的旋律。“古琴允许这样的行为,琴谱不是最终的结果,只是一个出发点,从琴谱出发,可以有很大的空间。”
杨岚的人生也和古琴曲一样,流动、灵活且充满变数。
他在黔西南一个叫作“安龙”的县城出生长大,按照他在书中的描述,那是一个除了南明永历小朝廷短暂的停留之外,与中国历史绝缘的地方,“有种原始的天真与粗暴,很难和什么古典意象牵连起来。”迷上古琴之前,摇滚乐填满了杨岚逃学时做的白日梦。直至今日,他依然觉得摇滚乐和古琴有着相似的反叛底色。但对一个懵懂天真的初中退学男孩而言,兴趣的转向迅速且自然:他对古琴的兴趣始于2001年央视版的《笑傲江湖》,那版的道具和配乐都使用了真的古琴,它的音色和所代表的隐逸文化立刻抓住了杨岚的心。在“山中弹琴”这一唯美意象的牵引下,他背着一把花了4500元买来的破古琴踏上了上山之路,彼时的他还不知道,琴学的中心从来不在山林而在城市。在山林寻师不得,反倒是给他的人生履历添了一处有趣的闲笔——在嵩山脚下习武。
18岁时,杨岚开始自学斫琴,以此作为一个在努力研习谋生手艺、让父母安心的保护壳。在家斫琴的那些年,他其实没有做出过一张真正的琴,他甚至对古琴本身无甚兴趣,也不会弹,他真正喜爱的是阅读和写作。以斫琴为借口,杨岚将大量时间花在了阅读上。他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和格里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的文学偶像,但也曾让他绝望地以为自己永远都写不出像样的文字。2009年,朋友邀请他去江南居住,他将手头未完成的琴全部付之一炬,来到了宁波雁村。不知不觉地,杨岚成为了一个“琴人”——2011年他带着游历的心思离开宁波来到杭州,因为喜欢这座城市的氛围定居至今,南宋时的琴学中心正是在此;他终于真正学会了斫琴,且能够每年做几张琴来养活自己;他与古琴名家成公亮结成了一种松散随性却感情真挚的师生关系;今年他开始尝试将工作重心从斫琴转向教学,并且计划举办自己的演奏会。
回想自己的少年时代,杨岚承认浪费了很多时间,但他认为,恰恰是这些“年少时做的无用功”让他成为现在的自己,并且给了他写作的灵感源泉。《琴人》的最初设想是一部古琴笔记,但在编辑的鼓励下,杨岚更改了初衷,写下了自己的成长史。他同样也认为,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有太多幸运的成分。无论是出于同伴压力也好,流行文化对所谓男性气质的规训也罢,十几岁的男孩脱离校园生活后太容易被那些暴戾的东西所吸引。杨岚也不例外,但他总能在自己很困惑或很危险的时候得到指引。“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跟你打架可能都打不过,”他笑道,昔日的危险阴影在他的身上早已了无踪迹。如果他不提,难以想象他也曾是个在街头闲逛、拿炮仗走到巷子里把别人家的窗户炸碎的“不良少年”。这本有可能会是杨岚另外一个版本的人生,写作《琴人》勾起了他诸如此类的小镇生活回忆,他说,会在下一部作品中用小说的形式去讲述这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在山中弹琴只是一个文人梦想,一个永恒乡愁——在认清这一点以后,他的现实生活和智识生活都取得了逻辑自洽。作为一个从边缘向中心流动的小镇青年,县城的生活经验一直是他看待世界的出发点,但他从未想过返乡,对故乡没有情怀,而是完完全全接受自己当下的生活。作为一个古琴演奏者,他承认凝结于古琴之上的崇古传统,却强调任何一首琴曲在当下被弹奏出来,就具有当代性。理想的古琴演奏是作为演奏者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存在的,而不是演奏者对某个古人的模仿或扮演,为此他坚称,自己永远不会穿着汉服弹古琴。在谈到如何理解“琴人”这个身份时,杨岚说,“古琴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乡愁。那些声音,在过去被一些人创作出来、演奏过,然后现在又被弹起,经由琴声,我们跟古人产生了一些联系。它并不是原来的声音,它是属于当代的,但依然有一些精神能在其中被感受到。”
01 叛逆者:年少时做的无用功,如今我已知晓如何转化为意义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了少年时代对摇滚的喜爱。摇滚乐和古琴是反差很强烈的两种音乐,前者来自西方、现代,又有反叛色彩;后者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古琴是如何在你十几岁的时候进入你的梦想,成为你的某种执念的?
杨岚:我依然把摇滚乐和古琴看作是气质相似的东西。古琴中有一种反叛的传统,嵇康、竹林七贤和《广陵散》其实是很反叛的。那时候的古琴就是“摇滚乐”啊。我没有把这两者看得那么对立。
界面文化:你次对古琴感兴趣是因为看了央视版的电视剧《笑傲江湖》。
杨岚:对,我们这代人都是受金庸影响的。所以我是一个受流行文化、当代文化、外国文化影响的人,它们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传统文化。“过去即异域”,我把传统文化当作一种“异域风情”。我不认为它是过去在我们当下的延续,而是把它当成另外一个空间的事情。我像一个旅行者一样去感受它,再回到自己的生活。
100%还原过去是一种完全徒劳的尝试。很多人对古琴有一种观点,觉得要保存古琴的“老味”,我们讲谁弹得好,会说TA弹得有老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你不可能有老味——一个年轻人,弹琴怎么可能有老味?你不是民国人,你听过凤凰传奇、巴赫和周杰伦,你的耳朵不是民国时代的耳朵,你的大脑和心灵也改变了,你不可能还原那个时代的东西。你必须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经验,如果不面对自己的经验,去模仿一个想象中的过去,那是虚伪的。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还提到,斫琴一度是你回避身份焦虑的一个保护壳,而亲人们也对此心照不宣。你能再谈谈你和父母的关系么?
杨岚:我当时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就是阅读和写作,但这个愿望我是不能和身边的人说的。即使父母很理解我,我也没有办法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很畅快地沟通。我就是通过斫琴告诉他们我有事情在做,但其实我只是假装在做这件事情,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看书。
如果没有家人,我很难有这样的生活。昨天我妈还给我打了电话。我现在比原来受到更多关注,她好像没有特别强烈的作为父母的高兴,反而希望我能回到一种更平静的生活,沉下心去做自己感兴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她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异议,这挺难得的。30岁左右的时候我基本就是过着维持生计的生活,她好像也没有强迫我去赚钱。我和她解释,现在时间宝贵,精力也比较旺盛,还是希望能学一些东西,她也尊重我。
界面文化:为什么你会觉得阅读和写作反而是件比斫琴更难沟通的事情,前者难道不是更“大众”么?
杨岚:对于一个小县城的公务员父母来讲,写作作为一种职业是更难沟通的事情,斫琴可以实实在在地做出东西卖钱,是更容易被理解的(笑)。他们已经尽量理解我了,尊重我的兴趣爱好、我的时间,但他们肯定希望我有一门养活自己的手艺,斫琴就是这么一门手艺。不过他们也不太相信我能斫琴,只是看着我好像很认真地在做这件事,会觉得踏实很多,比整天待在家里看书更让他们踏实。
斫琴其实挺重要的,它给了我很多丰富的生活体验,即实实在在地通过身体去劳作。我当时有点理想主义,向往通过劳作谋生、业余时间追求精神生活的那种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当时我对古琴没什么兴趣,我只是找到了一个东西来实现我瓦尔登湖式的生活理想。
界面文化:虽然说是在斫琴,但其实你在很长一段时间时间里没有做出过一张琴,而且还把那些没做完的琴用火付之一炬。现在回想过去,你会后悔吗?
杨岚:确实做了太多无用功了,但没有这五六年浪费的时间,就收获不到这些奇怪的经验。如果我走了一条很直线的、直达目标的路,我的时间浪费会降低很多,但我会失去很多这个过程中有意思的东西。这些有意思的东西如果不转化为另一种产出的话,就没有意义。现在对我而言,我知道怎样去转化它了,它就变得有意义了。比如说我用自己“无用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如果我是科班出身的人,我写的书会多无聊啊,我只能写几岁学钢琴、几岁上音乐学院、几岁参加什么比赛,这样的经历太普遍了。
界面文化:在各种意义上,你都是当下大多数年轻人的“反面”,对后者而言,浪费时间越来越是一种罪恶,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严丝合缝地为“上岸”铺路,而上岸这个概念已经泛化为人生中的大小目标,无论是升学、考研,还是考公、求职、结婚生子。作为一个跳脱出一般中国孩子成长路径的“叛逆者”,你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
杨岚:我之前交往的朋友大部分是70后,我从小就喜欢跟年纪大的人玩,我和长辈相处得很好,生活方式也是受年长者的影响。这两年我开始和很多比我小的人交流,有感觉到这一点。原来我可能会更持批判态度,但当我了解更多人的生活状态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们了。我不觉得大家都需要走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能在平常的生活中创造一些不平常的东西,给自己一些不平常的感受,或者以一种不平常的角度去看待生活,就好了。
我觉得我的成长经历没有什么可复制性,它其实是很危险的。那些和我一起辍学的伙伴,如今的状况其实比较糟糕。我在充满暴力、危险和毒品的复杂环境中成长,很幸运的是我见过这些,但完完全全地规避了它们,但换一个人可能就会被危险性拖住,拽入其中。(年轻人迷恋“上岸”)其实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大家的生活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生活的路径变得越来越同质化,要以个人的力量去对抗社会要付出很大代价。
02 琴人: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只要在当下被呈现出来都是当代文化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琴学中心从来不是山林而是城市,而这个认知偏差也导致你在学习古琴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这背后反映出来文化理想和现实基础的某种鸿沟:我们以为传统文化艺术隐藏在山林之中,但其实它也必须在经济发达、各种人群聚集的都市才有发扬光大的可能。可以说这是关于古琴的最大迷思或者矛盾么?
杨岚:隐逸一直是一种文人理想,这种理想与现实(特别是文人自身的生活)之间的撕裂产生了张力,这种张力是创作的源泉,如果离开了这种张力,只是过一种隐逸的生活,是没有创作的力量的。从南宋开始,古琴的中心在杭州,明代在常熟,清代在扬州,近代在上海,五十年代到了北京——古琴的发展一直都在城市,但想象的是山林。《樵歌》描述的是元兵破临安之后作者的隐逸之志,但作者毛敏仲去大都见了忽必烈求功名,因为此事被汪元量作诗嘲讽。山水画也不产生于山林,起码从明代以后,山水画最重要的中心是在经济文化最繁荣的苏州,文徵明、沈周、董其昌都是城市文明的受益者。
界面文化:这种都市和乡野的二元对立,影响非常深远,甚至直到现在。“崇古”似乎一直都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杨岚:最近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好像又复兴了,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开始想去乡村居住,过一种自然的乡村生活。但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能在此处获得平静,在哪里都获得不了平静;如果你不能接受现在的生活,那你就是不能接受生活本身,要到哪里找到平静呢?去了乡村会想要更好的乡村,去了更好的乡村又会觉得城市更好。人的习性就是如此,永远都不会接纳自己的生活,总会想要更好的生活状态、更好的生活环境,也许在这里,也许在那里,总是想找到一条途径摆脱自己现在的生活。
乡愁永远都会存在,但它和乡村没有关系,它只是需要找到一个地方来安放。在中国人的想象里,文明是从高处跌落的,永远今不如古,我们追求一个上古的淳朴时代,觉得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孔子就在批判他的当代,觉得一定要回到一个文王武王的“圣王治世”的时代。这确实能催生很多作品——在传统语境里,文人对理想诗意世界的想象令他们产生了很多创作冲动。如果这种理想的诗意世界只是文人的书斋梦想、一个枕头上的梦,它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如果它被政治化,和现实产生关联,就会变得非常糟糕。
中国文化里崇古是一种想象,通过想象去刺激自己的创作,这是一种方法论。古琴曲很多都是通过崇古来重新转化为当时的创作的,即通过想象古人来创作。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可以更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要有这种自觉,起码我会有这种自觉。
界面文化:作为一个琴人,你是怎么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呢?英国艺术史学者柯律格发现,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性这些二元对立直至今日都在左右我们对中国画的理解。“‘中国的’被等于‘传统的’(因此不是现代的),而‘现代的’则被视为一种模仿(因此也不是中国的)”——这句话似乎不仅可以用来形容中国画,也可以用来形容古琴。
杨岚:我原来也会困惑这个关系,但现在不太认为两者对立了;当两者不是对立关系时,我的生活开始统一。传统也好现代也好,我现在弹的任何一首琴曲都是当代音乐——只要现在被我弹出来,它肯定是当下的。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西方和东方,它们都是我的养分、我的经验,当我尝试做任何一种表达的时候,我都会带着这些经验。
而我最重要的经验还是小县城的成长经验。它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现代的,有点奇怪和荒诞,是我看待世界的最初出发点。我觉得这种荒诞让我能够对现代和传统有一种特别的感知,它们没有那么对立了,因为所有的东西——家族的记忆、传统的力量、外来现代文化的影响——都以一种很有趣很荒诞的方式扭曲在一起,没有办法分割开。在我的经验里它永远是新鲜的,永远能激发我的某种热情。
界面文化:这几年国潮的风头正劲,许多年轻人重新从传统中寻找文化资源。关于民乐创新,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杨岚:把东方音乐移植到现代音乐,这是很多严肃音乐家从60年代开始尝试的事情。但它不会是一种简单的移植,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60年代的极简主义音乐受印度音乐、巴厘岛音乐的影响很大。西方古典音乐到了20世纪其实走到了绝路,坂本龙一曾经说过,他放弃严肃音乐的作曲很重要的原因是觉得古典音乐已死,之后的音乐趋势是电子音乐和民族音乐。整个20世纪后半叶,作曲家都有两种倾向,一是学习东方音乐、非洲音乐这些非西方中心的音乐,二是电子化。
民乐的现代化是音乐发展的必然,但我们和西方人不一样,他们可以很轻巧地把东方音乐拿过来做,我们有点困难。作为文化主体,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把我们的东西变得更现代。这是因为我们不熟悉现代音乐发展的脉络。很多音乐学院的教育也是这样,学的是古典音乐,至多到20世纪初,对现代音乐的内在理论我们是很陌生的。有一种倾向是认为现代化就是流行化,那首先就要把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分开。
成公亮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学习了很多中国戏曲,又了解很多别的音乐传统,他把印度的旋律拿过来,用古琴的语言表达出来。我认为,用古琴创作乐曲的时候,首先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要用古琴,古琴的特点我们肯定要保留住。成公亮先生用古琴的语言来创作印度风格的琴曲,是因为他找到了古琴和印度音乐共同的节奏特点,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作了新的琴曲。
另外,古琴其实还没有在表演上成为一个业态,它还是一个很松散的形式,还不存在一个规范的表演形式。这是很多古琴演奏家的困惑,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在公众面前呈现古琴?我们是在介绍古琴,还是让大家对“我”感兴趣?我觉得表演上应该可以做得更有意思一点。
我比较喜欢日本作曲家武满彻,他是一个纯粹的现代作曲家,学习的是20世纪西方先锋音乐。他也为日本传统乐器作过曲,像雅乐、尺八。他的作曲方式技法是现代的、西方的,但是出来的味道又完全是日本的。我们总是把传统等同于过去,但我觉得任何一种传统的文化,只要在当下被呈现出来,都是当代文化。而空间上不同视角的转换,可能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东方。
界面文化:如今你如何理解“琴人”这个身份呢?
杨岚:我希望自己在古琴和写作这两件事情上都更加够格,但我的身份一定是琴人。我虽然一直靠琴谋生,但原来有点抗拒这个身份。因为我感兴趣的事情很多,觉得古琴的世界有点狭窄。而当我对很多事情发生过兴趣之后,带着这些经验再回到古琴时,发现它其实很开阔。但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现在我有了写作这个通道,有了另外一个跟时代和社会连接的方式,因而可以把琴放回到更恰如其分的位置。
古琴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乡愁。那些声音,在过去被一些人创作出来、演奏过,然后现在又被弹起,经由琴声,我们跟古人产生了一些联系。它并不是原来的声音,它是属于当代的,但依然有一些精神能在其中被感受到。我希望能够把我在其中获得的体验传达给他人,这也是一种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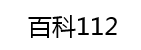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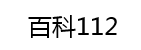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燕赵河北麻将开挂多少钱”(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燕赵河北麻将开挂多少钱”(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