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河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2023年6月2日,总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总概括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既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提炼,亦架起了历史与现实相联结的彩虹。中华儿女对于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要传承弘扬、守正创新、与时俱进,要扬起时代风帆破浪前行。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六大原生形态文明(中华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美洲玛雅文明、南美洲印加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从五千多年前诞生伊始一直发展到今天,一直在传承、创新和发展中。中华文化和文明延绵不绝,产生了许许多多原创性思想并形成自己的文化基因,孕育出一批又一批经天纬地的杰出人物,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若从政治文明、形态结构和发展道路着眼,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阶段经历了“聚落三形态的演变”: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距今10000多年到距今6000年),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距今6000年到距今5000年),再发展为都邑形态(距今5000年到距今4000年),这属于五帝及其之前的时代。进入之后,形态经历了“邦国—王国(三代王朝)—帝国(帝制)”三大阶段;结构相对应的是:五帝时代单一制的邦国—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复合制的王朝—秦汉至明清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中央—郡县”一元化的统一多民族。与此相对应,在族共同体上经历了“炎黄—华夏—中华”的演变历程。中华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交往,并不是封闭的,但她从起源和形成开始就既是本土的亦是多源的,多源合流,形成了多元(源)一体;在之后漫长的发展中与外界的交往因时而异,但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只是在吸收过程中很快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对于世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参照系作用。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所表现出的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勇于接受新事物、与时俱进的风范,是伟大的。这一点同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致的;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一致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属性的概括,其中要达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必须对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文化传统的变化,有两种机制:其一,传统文化每每随着自身所在社会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其二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而补充新鲜血液、焕发新活力。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传统文化,一般是采用“扬弃”的方式而弘扬其精华、丢弃其糟粕。通过吸收外来文化而变化的传统文化,通常是与“异质”的不同文化相融合而走向创新发展。这种融合也表现为外来文化通过“内化”(中国化)融入社会。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特别需要融入科学文化的。这是因为从时代性上讲,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基础上的。近代以来,历史的火车头是由工业文明驱动牵引的,特别是当代已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我把它称为“新科技文明”。所以,当代与中国式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文化建设,特别需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融合。也就是说,继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按照惯性只是固守传统文化向前行,而需要科学文化的加入。
通过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融合来实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一是要坚持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原有的价值体系中加入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价值观;二是要把科学研究中实事求是、追求真实、追求真理的科学探索精神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三是要把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四是要在大学本科的教学中,以紧追科技前沿的要求经常更新或引进优质教材,传授新科技文明最新知识,使大学系统的基础教育与科技发展前沿相衔接,培养学生的创造创新能力,以适应新科技文明的社会需求。这样,只有将科学价值观、科学探索精神、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新科技文明知识体系融合到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才能使之成为当代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当代中华文化建设方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需要,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所呈现出的统一、民族凝聚和文化融为一体,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认同”与“民族凝聚”的必然要求,此乃一体三面关系的国情所在。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形成的发展过程来看,“炎黄—华夏—中华”是其阶段鲜明的历史轨迹。在这样的轨迹中,“中国”与“中华民族”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时间,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就认为中华民族是从近代才开始形成的。费先生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大阶段:作为“自觉”的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多民族起,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就已经形成。从秦汉到明清,在统一多民族内包含两个层次的民族共同体:一类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一类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当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也即在统一多民族内,汉族是主体民族,少数民族始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朝代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是由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
从秦汉到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包含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其最基本的条件就在于以郡县制为机制的统一多民族结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结构内,中华民族才既是多源的又是统一的,是“多源合流”,其统一性是由的统一而规定的,离开了统一多民族结构,离开了统一的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就无从谈起。
从秦汉到明清“郡县制”这样的体制机制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形态结构,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的基本特征。郡县制解决了两千多年帝制王朝直接管辖地区的行政管理,也在结构上维护了多民族的“大一统”形态。在这样的行政区内,汉族是主体民族,也包含少数民族,也就是说,郡县之内已有不少地方民族杂处。这种由郡县制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以及由作为文化的汉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则可以逐渐融化郡县制行政区域内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异,并进而走向民族融合。在郡县制行政区域之外的边疆地区,除了“夷汉相错而居”之外,两千多年的帝制王朝在边疆区域的行政体制上,经历了从“羁縻”政策到“土司”制,再到“改土归流”或移民实边或直接管辖,使边疆地区在逐步实现“封建化”的同时,也走向与内地“行政一体化”。边疆之所以能够逐步走向与内地一体化,就结构而言,内地郡县制的行政区域是主体力量,“中央—郡县”一元化的体制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欧洲在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民族(nation-state),其中有的是以一个主体民族为主,也包含少数其他民族的民族,有的是几个民族联合的民族。中国则是自秦汉开始就形成了一个统一多民族,作为从“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央—郡县”一元化的体制是中国历史道路显著区别于中世纪欧洲的地方,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机制也与近代欧洲的民族很不相同。
中华民族是由从秦汉开始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统一结构造就的,以统一的为框架,是一个与统一的互为表里的全中国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历史是这样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为此我们说,“中华民族”与“中国”二者所具有的一体两面的关系,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所在,是由中国历史上与民族的内在关系所规定的。
如果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从秦汉开始形成的,那么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则是汉族和中华民族的前身。汉族在秦汉以来是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主干或基干而存在的,当我们对作为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汉族溯源时,可直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华夏民族。在主干的意义上,从先秦到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呈现出“炎黄—华夏—中华”这样的演进轨迹。在这样的演进轨迹中,每个阶段的族共同体的类型都有相对应的形态结构:与“炎黄族团”相对应的是五帝时代的单一制的部族;与“华夏民族”相对应的是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对应的是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形态结构。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民族个性,亦是文化特征;既是历史,亦是现实。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每每呈现为中华文化的多彩一体性。中华文化既是多彩的,又是一体的。其“多彩”指的是它由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民族文化所汇聚,既包括了汉文化向边远民族地区的辐射,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向中央王朝的汇聚; “一体”既指它的载体的一体性,又指它在文化这一层面上是一体的。所谓载体的一体性,是说中华文化以通用语言文字——汉语和汉字为其载体,汉语和汉字就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初期所说的“国语”“国文”。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建立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时,特意统一了文字,使得两千多年来汉字和汉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文化,亦是文化,成为维系统一和中华民族统一的纽带。
中华文化的“多彩”与“一体”也是一种辩证关系:“多彩”使得“一体”颇为丰富且“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容许差异性存在的,它为中华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一体”使得多彩是有序的整体,是与文化合而为一的。所以,“多彩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在一体性中有主体又多彩多样的文化形态。
中国历史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表现在文化上则可称为“互化融合”。历史上,对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而言,每每走上了“汉化”的道路;而对于汉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而言,则应称为“互化”。“汉化”是沿用以往一般历史著述所使用的概念,但实际上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我更愿意使用“互化融合”这样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文化的互化,指的是原有的汉文化因少数民族文化的汇入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而发生的改变。在中华文化里,既有少数民族汉化的一面,也有各民族文化互化的另一面,汉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壮大是互化的结晶。无论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还是秦汉、隋唐、元明清的统一时期,中国历史上灿烂的文化和文明都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走的是文化互化与文明共建的道路。仅以在音乐和文学艺术方面汉文化因吸收少数民族文化而获得发展为例,从南北朝到隋唐在北方流行的所谓“胡歌”“胡乐”“胡舞”“胡戏”,最后都融进了汉文化,成为汉文化的组成部分。北朝的音乐直接影响了唐代的乐曲,唐十部乐中的燕乐和西凉乐大多来自北朝的胡汉混合乐。北方河朔文化和南方的六朝文化一起,构成了唐代高度发达的唐文化的两个来源,隋唐灿烂的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元朝的戏曲、散曲、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它却是各民族文学艺术交融的结果,是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影响和对中华文化贡献的又一显例。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并通过互化而形成的汉文化和中华文化,其所具有的凝聚力,因其许多思想内涵具备超越时空的价值,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还表现在外来文化中国化之后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儒释道三个方面,儒家和道家是由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文化,自不待言。佛教是由外传入中国的,但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就中国化了,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在于中华文化本身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对促进中华民族内各族的跨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以及各种矛盾的协调,形成了很大的弹性,取得了超常的成效。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在历史上起着凝聚人心、吸收外来文明的作用。到了当代,它不但依旧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土壤,而且还会使中华文化与时俱进、融入“新科技文明”的潮流之中。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内部是强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要讲究和合,其特质是“和而不同”。例如,《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在和谐中保存了差异性,也就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提,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为了和平,社会就得讲荀子所说的“礼法”。《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礼的实行和治理,都以“和为贵”。中国的儒释道都主张建立和谐社会。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尚书·尧典》说“协和万邦”,《礼记·礼运》讲“天下大同”。今天,我们讲文明互鉴,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追求和平,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普遍心声。因为追求和平,在战国七雄掠夺嗜杀时,人民希望统一。《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者能一之。”这里的“一”就是“统一”。这段话清楚地表现了战乱时代人民渴望统一的心愿。因为追求和平,今天我们讲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愿和平发展永远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旋律!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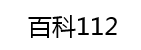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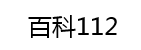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瓜瓜丰城棋牌怎样提高胜率”(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瓜瓜丰城棋牌怎样提高胜率”(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