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渭南日报】
李康美
在渭南文学界,提起十二行诗,朋友们立即就会想起徐喆。一个诗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招牌,终于有了专属于自己的创作形式,这无疑是徐喆在文学创作中的成功之处。现在,徐喆又以十二行诗的固定格式,出版了《岁月的包浆》,这是诗人的成熟,这也是徐喆的坚定和自信。其实,徐喆对于十二行诗的试验和探索,已经走过了起码十年以上的路程。在2015年渭南市第二届杜鹏程文学奖的评选中,徐喆的诗集《蓝色十二行》就获取了当届诗歌类大奖。一部作品,从日常创作,到结集出版,再到评奖参评,都有一个间接的过程,所以说《蓝色十二行》就肯定是多年创作的思考和积累。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当年的研讨会上,我以《蓝色十二行》的诗歌体例发言说,所有的文学和艺术,都是从借鉴前人开始,然后才有后人的探索和创造。工业文明如此,农业文明如此,网络化文明如此,文学创作同样如此,尽管需要创新,但是千万不能忽略,最不能缺少的仍然是要去认真地寻找和汲取前人的聪明和智慧。
说起徐喆的十二行诗,凡是从事诗歌创作的人,都会联想到曾经风靡于欧洲的十四行诗。十四行诗起源于意大利,后来又在整个欧洲流行。从14世纪到16世纪,享誉西方诗歌界数百年之久。先是意大利人彼特拉克把十四行诗锤炼得炉火纯青,后来的英国人莎士比亚和俄国人普希金也都是十四行诗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在这里,我不想罗列更加详实的资料,也不想叙述十四行诗的体例和严格的讲究。但是有一种现象让我印象深刻,同时也引起我浓厚的兴趣,这就是根据西方人的研究,十四行诗也是从民间起根发苗,最初反映的只是劳动人民的社会风貌。这就让我想起中国的诗歌发展史,想起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而《诗经》同样来自于民间,先是口头吟诵,后来又由古曲传唱,慢慢地就形成一种文体,然后再由有心人汇编成册,进入宫廷,走向正统。《诗经》的作者都没有姓名,那是因为后来的《诗经》已经不是原生态,不知集多少人修改,补充,去粗存精,韵律讲究之大成了。
文学艺术,都会涉及结构问题。在理论界,甚至还把文学艺术的结构划分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非常高深的分门别类。当然,作家和诗人,大可不必被那些东西束缚和恐吓,只需要在创作的过程中,形成自己文本结构的自觉。实际上,毋庸讳言,结构也可以理解为形式,用我们普通的文学思维来说,不管是结构还是形式,其目的都是增强作品的美感,都是属于文学的审美范畴。
从《蓝色十二行》到《岁月的包浆》,徐喆的诗歌创作,叫结构也好,叫形式也好,叫模式也好,都显然产生了文体创新的意义。阅读《岁月的包浆》,可以看出徐喆在十二行诗的总体坚守之下,其内在结构当然也带有规律性的变化:其一是四句三节式;其二是三句四节式;其三是六句两节式;其四是两句六节式;其五是十二句一统式。而且还有少数作品,前节是五句,后节是七句式。从而可见诗人的固守和多变。固守的是十二行,多变的是内在的不断转换。
那么,我们还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在十二行诗的句式变化组合中,外表和内容,诗体和诗质,有没有什么自然或者必然的联系?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是为了变化而变化,那就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粉饰;如果是和内容相照应,那就是一种有机的结合。为此,我欣慰地得出的感觉是,徐喆在对每一首诗的构思和写作时,同样也不时地提醒自己,如果把一首诗比作一个人,首先要弄清这个人的性格、涵养、气质,然后还要琢磨他或她应该穿什么衣裳,戴什么首饰,搭配得当,才会得体;搭配得当,才能达到结构和内容的统一。比如说,《杏花说》和《又见梨花》这两首诗都是写花,但是《杏花说》的体例是前节五句后节七句式,而《又见梨花》则是十二行一统到底没有分节。如此的不同,只有仔细研读才能看明白。《杏花说》是把“杏花”拟人化,前节是心理的期盼和呼唤,后节是满足的喜悦和。而《又见梨花》则完全是描述“梨花”和观赏者的互相感应,既然阐释的是天人合一,文体也就是无缝衔接了。当然,徐喆的文学之旅,已经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他对于社会的认识,对于人情人性的思考,都必然会发生质的飞跃。在这里,我只是对徐喆十二行诗的文体和结构形式作出自己的解读,至于徐喆的语言系统,思想内含,抑或还有其他的收获,读者们也会作出自己的见解。
本文来自【渭南日报】,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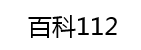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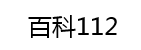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嗨岛麻将怎么知道别人开挂”(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嗨岛麻将怎么知道别人开挂”(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