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敬畏生命思想的时代意义
为了引起更多的学者研究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的兴趣,不仅有更多的文本翻译和解读,而且有更多的对其思想的阐发、探讨和比较,笔者拟对施韦泽敬畏生命生平和思想的时代意义,从道德个人主义、文化伦理主义、生命自然哲学和中国思想等四个方面作简要的发挥,以为本书的“结语”。
一、 道德个人主义
本书篇“伟大人格”给出了一个关于理解施韦泽人生和人格的图景和解读,对于中国读书界和学术界的相关思考和研究还是有益的。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图景和解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国式”的,即主要从其人格和文化理想与中国文化的“亲和性”角度着手的,对于其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涉及得则较少。虽然就施韦泽不凡一生和伟大人格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言,“亲和性”方面固然重要;因为正如中国古人所说,无论东海西海,圣人的心是相通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陆九渊集·卷三十六》)但显而易见的是,为了吸取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以刺激和推进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了解和反思其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方面,也许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以下拟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两个方面,对施韦泽人生和人格的时代意义,作进一步的探讨。
施韦泽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不会有异议。但是,正如在比较施韦泽和梁启超时已经初步指出的那样,就涉及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同样作为道德高尚的人,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差别就很大。例如,中国古代的道德典范诸葛亮和岳飞,都首先是政治人物,然后才是道德人物。而施韦泽则是一个道德人物,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艺术家和学者,但不能说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当然,施韦泽不仅思考政治问题,而且也并非完全不参加政治活动。不过,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自己与政治的关系,必须直接从其工作和其对神学、哲学、音乐的思考中产生。从而与卷入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相比,施韦泽更愿意与涉及全人类的问题打交道,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一个愿意与别人对话的人。应该说,中西道德典范的这种区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施韦泽继承了耶稣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基督教个人道德传统,诸葛亮、岳飞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道德传统的体现。这两种传统各有长处和弱点。儒家政治道德传统有助于中国古代政治的改善,对中华民族可大可久之生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也有使知识分子过度关注政治生活,而忽视其他社会领域活动的弱点。基督教个人道德虽然不着重直接改善当时的政治,但它为人们从事社会领域的道德活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例如,施韦泽虽然不直接从政,但由于其治病救人道德活动的广泛影响,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影响甚至也渗透到政治领域。事实上,政治活动不仅并非人人可以从事,而且不宜人人从事。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发扬古代儒家政治道德传统的同时,还应该摆脱过度的政治道德中心论,拓展自己道德活动的领域,在即使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在工商经营、福利慈善、社会研究、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等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这么做了,这样就也许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当然,就施韦泽人生和人格对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时代意义而言,更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则是其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思想。例如,在比较中西世界观时,国学大师钱穆明确地指出,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则看重整体:“部分从整体生,不明其整体,即无法了解其部分。这是中国人观念。”[1]这就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确定了在个人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人注重整体即“社会”的倾向,应该说是有根据的。此外,在一段时期内,中国也曾经出现过把集体主义等同于大公无私,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的观点,似乎既体现了中国人注重整体“社会”倾向的影响,也反映出某种激进和偏颇的看法。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作为一个公认的道德高尚人物,施韦泽却反复强调要“坚持绝对个人和独立的行为”,“要作为个人和自由人而奉献”,表现出一种绝非“自私自利”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奉献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即“道德个人主义”的倾向。那么,对比如此鲜明的中国重整体社会和西方重部分个人的伦理观点,究竟哪种更为合理呢?对此,笔者认为,中国重整体社会的道德传统自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如果能够自觉地吸取诸如由施韦泽“道德个人主义”所体现的西方重部分和个人传统的积极因素,就会在当代中国形成更合理的道德生活以至整个社会生活。
这就是说,在个人与整体、社会的关系上,在个人与的关系上,如何更多地发挥个人的自由个性和独立思想,防止物质主义文化对人的思想能力的削弱,防止公共关系的过度化导致个性在集体中的萎缩,防止整体的非道德化导致个人的迅速非道德化,把责任奉献和自由个性统一起来,我们确实可以从施韦泽的行动和思想中获得重要的启示。此外,在这方面,施韦泽关于“伦理的个人伦理提升社会的伦理”的思想也是发人深省的。在中国的道德传统中,我们通常的思维模式是个人对社会伦理的服从,而忽略了个人对社会伦理的提升,这样实际上也就可能忽略了:真正的人道、真正的伦理进步是由富于道德创造力的个人来推动和实现的。因此,这种过多地基于现实社会秩序及其管理角度思考道德问题的路径,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忽略了施韦泽关于社会伦理、公共行动往往只与集体利益能够直接联系的事实相关,而个人伦理则与更为重要的“创造促进集体的信念”相关的思想,确实也会造成许多弊端。因为个人可以通过自愿牺牲而实现人道,但社会则可能会以无情规律的名义要求个人牺牲,从而蕴含着非人道的危险。施韦泽这些明显具有异质性的思想,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进一步说,施韦泽不凡人生和伟大人格的“道德个人主义”,不仅表现为其个人直接道德活动中的“责任奉献和自由个性的统一”,而且也体现在他对文化和文化人类理想的探寻和追求之中。一个道德人物首先应有其直接的个人道德活动,这是最重要的,否则就不成其为道德人物。但是,如果一个道德人物,在其本人直接的道德活动之外,还有对社会、和人类理想的探寻和追求,那就更全面、更深刻了。必须肯定的是,施韦泽就是这样的一个伟大人物,他对文化和文化人类的探寻和追求,同样对于我们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在当代市场经济达到了空前程度的全球化之后,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似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各种社会理想都被作为乌托邦而被人们扔在一边。在这样的情势下,是否应该仍然坚持探寻和追求崇高的社会理想?我们对此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在此,施韦泽坚持和发展欧洲启蒙运动追求个人和人类趋向完善的目标、世界公民和人类博爱的目标,反对西方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反对市场经济无限制的物质主义,反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化,反对大众流行文化的浅薄化,倡导要按照文化的伦理本质来建构现代,向人们提供生存和行为的优良的物质和精神前提,以最终达到完善的文化人格、文化和文化人类的境界,特别是在晚年还努力进行了反对核武器的斗争,从而成为一个追求崇高社会理想的典范。这一切对于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国民经济有了迅猛发展,有必要对今后的发展道路作些思考的21世纪的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来说,同样都是富于启示性的。在努力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更自觉地坚持文化的伦理本质、的伦理本质,更自觉地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的社会理想,既能够捍卫自己民族和的权益,又善待其他民族和的权益,以走向天下太平的文化人类目标,与其说是多余的,毋宁说是不仅与中国的未来,而且也与人类的未来都是命运攸关的。这里,由于施韦泽的文化和文化人类理想既与中国儒家的社会理想相关,又与西方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相关,尽管至今人们对其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太多,但确实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和理想。
二、 文化伦理主义
如果说,施韦泽的不凡人生和伟大人格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特殊的道德个人主义,那么其文化哲学的核心观点则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伦理主义。所谓文化伦理主义,作为笔者对其文化哲学思想的一种概括,用我国当代学术界通行的哲学术语来说,指施韦泽坚持认为,相对于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伦理道德对于文化的命运,对于个人、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才是最重要的,是决定性和本质性的。而相对于在当代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以货币为普遍交换媒介的市场经济生活而言,不同于其把追求国民总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增长作为主要目标,文化伦理主义则强调这些经济性的增长,特别是货币的增值要服务于人的精神和道德完善的目标。至于用施韦泽自己的学术语言来讲,文化伦理主义指文化包括知识和能力、各种生活关系、个人的精神和道德三个层面,其中只有个人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才是文化的本来和最终目的: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不是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是伦理,即个人思考人、民族和人类及其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和有效地为这种理想所决定。这显然是一种与道德个人主义相关的对于文化本质的特殊和重要的理解。众所周知,在人类思想史中,对于文化本质的理解,人们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如有的着重个人幸福,有的着重整体德性,有的着重天国信仰,有的着重自由权利,有的着重经济发展,有的着重审美创造,等等。这些不同的视角,分别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文化本质的看法,都有其合理方面,并由此构成了人类的文化创造及其理解的不断发展着的总体图景。当然,就其中的某一特定看法而言,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不可能穷尽人类文化创造及其理解的所有向度和功能。因此,把握文化本质的合理态度是,尽可能广泛地容纳各种视角,并在特定的情况下重点选取某种视角,避免片面性,力求全面性,以利于文化的当下和未来的发展。
基于这一态度来进一步考察文化伦理主义,就可以发现,施韦泽坚持文化的伦理本质,就是要坚持这样一种基本信念:文化是每个人应该在尽可能合乎人类尊严的生存条件下达到真正的人性,就是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就是敬畏生命。具体说来,要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合乎人类尊严的生存条件”,就必须有知识和能力以及各种生活关系的进步,因此施韦泽充分肯定和积极追求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所有进步,包括知识和能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人的社会化(社会关系)的进步,主张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的适度增长。但是,他同时强调,只有在服务于“个人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的前提下,这种进步和这些增长才是真正的进步,才可能成为“尽可能合乎人类尊严的生存条件”,并由此形成“达到真正的人性”的现实基础。因为知识和能力的进步具有既可能为进步服务、又有可能为野蛮效劳的双重性质;而任何现实的社会关系则更多地涉及与集体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实,而往往会忽略更为重要的与“创造促进集体的信念”相关的思想;至于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的增长,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能发生异化,并不能够自动地保证实现“个人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这一文化的真正目标。从而在思考文化问题时,人们必须自觉地坚持其伦理本质,使知识和能力与社会关系的进步、物质财富和物质消费的增长成为每个人达到“真正的人性”、“人性的圆满”的真正基础,而这么做的必由之路就是敬畏生命。这样,施韦泽就明确了其文化伦理主义的内涵、功能和地位,突出了作为“真正的人性”、“人性的圆满”的实质与核心的“个人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在人类文化中的最重要、最本质的地位。对于施韦泽的文化伦理本质主义,虽然不能说是无懈可击;但应该承认,这种文化的伦理本质论确实有助于人们更重视并努力发挥精神和道德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目的性地位和引导性功能。
就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比较而言,文化伦理主义类似中国的儒家思想。例如,“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第二》)[3]这里的孔子德治思想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领域的文化伦理主义。当然,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施韦泽的文化伦理主义特别接近中国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具有现代意识的儒家弟子梁启超的文化观念。20世纪20年代,与施韦泽发表《文化哲学》的时代背景类似,都是思考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文化建设,梁启超也认为关键要解决好“个性与社会性”、“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这两大问题。关于“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梁启超强调:“宇宙间曾无不受社会性之影响束缚而能超然存在的个人,亦曾无不藉个性之缫演推荡而能块然具存的社会。而两者之间,互相矛盾互相妨碍之现象,亦所恒有。……如何而能使此日扩日复之社会不变为机械的,使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能与时骈进而时时实现,此又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4]对照以上笔者关于施韦泽“道德个人主义”的发挥,可见这两位思想家的心灵是相通的,但这里重点考察梁启超关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关系问题的深刻探讨:“吾侪确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其有精神生活。但吾侪又确信人类精神生活不能离却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吾侪又确信人类之物质生活,应以不妨碍精神生活之发展为限度。太丰妨焉,太觳亦妨焉,应使人人皆为不丰不觳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5]人的本质在于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应该助成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向上,这一观点显然与施韦泽类似。至于道德和伦理,梁启超也予以最高程度的重视,他在中年和晚年就撰写了大量直接涉及“新民德”的论著。当然,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大力倡导“开民智”和“鼓民力”,要求国民提高艺术修养和审美趣味,与施韦泽重点强调人的道德完善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与其说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别,毋宁说是基于文化发展背景不同而形成的关注焦点的差别。梁启超面对的是近代中国救亡、启蒙、改革、建设等多重主题,因此在“新民德”的同时,必须“开民智”、“鼓民力”;而施韦泽反思的则是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化的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偏向,以至于爆发了次世界大战的文化衰落,因此有必要特别强调道德和伦理的本质与核心地位。
比较施韦泽和梁启超的文化思想,施韦泽坚持严格的文化伦理主义,梁启超则坚持更为广泛的文化精神生活本质论,但肯定文化伦理主义,甚至还对“新民德”予以了最高程度的重视。这一切不仅说明这两位思想家之文化观念的相互接近,而且更启示我们,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本质理论的坚持,都不应该教条僵化,而是要善于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其他文化本质主义观点相辅相成,以实现当下和未来的真正的文化目标。即使对于施韦泽的文化伦理主义,也应该持如此态度。就当代中国的情况而言,在经过偏激僵化的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普遍贫困时代之后,由于迫切的经济发展需要,三十余年来,中国特别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注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特别注重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这是十分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如贫富分化过度、生态环境破坏、贪污腐败蔓延、文化庸俗低下,等等。这就表明,当前社会似乎出现了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物质主义、消费主义、金钱至上等文化偏差倾向;因此,施韦泽的文化伦理主义对于我们合理地处理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有益的启示。确实,文化与政治、军事、经济之间的关系,还有高雅文化和普通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之中,始终是一个难以两全的问题,似乎往往只能把重点放在某一方面。但是,我们并不可以因此而放弃为较好地处理这一问题的努力,特别是在当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尽可能使经济强大和生活富裕“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的目标,服务于“个人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这一“文化的本来和最终目的”,使高雅文化引导和提升普通文化和大众文化,使普通文化和大众文化丰富和推进高雅文化。在此,施韦泽的提示不也是很有意义的吗?而从理论上说,这就把在坚持发展生产力、提高公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应该更重视精神文化和道德建设的历史性课题提了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取文化伦理本质主义的态度,但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则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文化的生产力本质主义和物质财富增长本质主义。因此,为避免文化发展的偏差以至于衰落,当今更要看到文化伦理本质主义的重要性。[6]
施韦泽的文化伦理主义不仅体现为一般的理论界定,而且充分体现在他对基督教伦理本质和歌德伦理思想等的深入研究中。面对传统教义的局限,施韦泽坚持“耶稣宗教”即“爱的行动伦理”而非“教义宗教”;在传教和教会的真正使命问题上,他要求“紧密地把宗教和人道结合起来”,首先要“使人成为人”,而不是只想到传播自己的宗教;在宗教的论证方式上,他坚持“基督徒认为伦理的宗教更有价值”、“伦理的宗教是最高的宗教”。这些命题不仅集中地反映了施韦泽对基督教伦理本质的强调,深刻地体现了他对“文化教会”理想的追求,而且对于我们观察和思考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大宗教以至其他各种社会的伦理本质并发挥其伦理功能,都是深有启示意义的。施韦泽对歌德“将生存目标为人性的圆满”之伦理思想的研究,则体现为对以下四个命题的重点发挥: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在实际行动和精神创造的并存中实现人格的统一。应该说,歌德的人格并非没有缺陷,但“人要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毕竟是其宏伟人格的集中体现。这一概括反映出施韦泽十分尊崇歌德“关于高贵同时就是善良的观念”,而对尼采的不能结合“高贵和善良”的超人思想则提出了批评。显然,这种“高贵和善良”相结合的人格思想及其理想,对于经济生存竞争剧烈和文化庸俗化的当代世界中的人格塑造,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是一种“高山仰止”的典范。而“不以正义为代价去做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凡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有所思考和感悟的人,都会体验到这一思想的重要性。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代人类“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已经不仅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也致命地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当代人类在做有能力做的事情时,更应牢记歌德“不以正义为代价”的思想遗产。此外,个人要通过坚持个人的理性理想以实现社会正义,即做到“高贵和善良”与“为正义担忧”,就必须“在实际行动和精神创造的并存中实现人格的统一”。可以说,这对于任何有道德追求和真善美圣理想追求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须臾不可忘却的启示:努力从事多方面的活动,把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空谈和片面,做一个行动的人道主义者。至于“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则不仅是歌德的宏观宇宙伦理,而且也涉及了施韦泽本人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深层基础。当然,对于这一深层基础的探讨,已经超越了施韦泽狭义的文化哲学范围,而进入了理解其整个哲学和伦理思想突破的关键所在。
三、 生命自然哲学
就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的突破而言,与“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相关的论述,可以说是施韦泽对于西方哲学思想以至整个人类思想的最重要贡献。对于这一突破和贡献,笔者把它概括为“生命自然哲学”,并认为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地位。关于西方哲学思想以至整个人类思想的进程,我国当代哲学家张世英参照现代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把“天人合一”还是“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指出这两种关系在中西哲学史上表现为三个阶段:个阶段是不包括‘主体—客体’在内的‘天人合一’,即‘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第二个阶段是‘主体—客体’,这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导原则。第三个阶段是扬弃了‘主体—客体’式的‘天人合一’。”[7]在我国思想界扬弃了“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对子的框架之后,张世英对西方哲学发展进程的概括已经为比较多的学界同行所接受。应该说,这也是我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认知和理解的一种进步。但是,如果了解了施韦泽对西方自然哲学和体系哲学两种哲学的划分;那么,我们对西方哲学及其与东方思想关系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化,也将更易于理解施韦泽的“生命自然哲学”及其在西方和人类思想史中的地位。在施韦泽看来,西方存在着两种哲学传统:自然哲学和体系哲学。自然哲学自古希腊泰勒斯开始,中经伊壁鸠鲁、斯多葛主义、布鲁诺到斯宾诺莎、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和歌德;体系哲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笛卡儿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前者为出于对自然研究以解释自然的非教条哲学,后者为把自己关于自然的观念强加于自然的教条哲学。当然,在歌德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使自然屈服于人的思想的体系哲学,而不是要求人顺应自然的自然哲学。但是,在19世纪中期思辨的教条哲学体系破产之后,彻底地思考自然哲学,并由此论证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施韦泽认为这正是自己的使命。这里可以看出,尽管与海德格尔的用语有所不同,但施韦泽同样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甚至更早地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吸取东方思想的智慧,论证一种既保留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哲学的积极成果,又扬弃了其局限的“后现代”哲学,以实现西方以至整个人类文化重建的目标。当然,显而易见的是,由于道德个人主义和文化伦理主义的敬畏生命原则,在当代世界,施韦泽的“生命自然哲学”比海德格尔的思想具有更深刻的道德意义。[8]
在提出施韦泽的“生命自然哲学”概念,界定了其历史地位之后,就可以探讨它的基本内涵了。首先,不同于以思想强制自然与世界的思辨哲学,生命自然哲学坚持“对自然现实的敬畏”,承认自然是自在的,而不是仅仅相对于人而存在的东西。就此而言,生命自然哲学似乎是一种唯物主义,告别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人为自然立法”的唯心主义;但也仅仅就此而言而已,超越了这一点,它就不再是近代的唯物主义了。这么说的根据在于,对于生命自然哲学来说,与承认“自然是自在的”命题相比,更重要的是要坚持:自然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着的,不仅是机械性的过程,而且还是生命,奥秘之奥秘在于生命之中。在施韦泽看来,现实的、充满生命的自然概念应该取代无生命的自然概念。那么,施韦泽为什么要如此说,他又是如何得出其有生命的,而非如同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那样的无生命的自然哲学概念的呢?对此,笔者认为,要理解这一思想,就有必要澄清其“生命自然哲学”的论证逻辑:作为最基本的关系,人与自然有两种关系,外在的认识关系和内在的体验关系。通过对自然的认识,人只会与自然发生外在的“生存竞争”关系;只有通过对世界的体验,人才能够与自然建立精神和伦理的关系,即内在的“敬畏生命”关系。而人为从与自然外在的生存竞争关系转变为与自然内在的敬畏生命关系,就必须实现从认识到体验的转变:“认识能够给予人的始终是这样的知识:在人周围的时空中作为现象出现的一切,就其本质而言,像人本身一样都是生命意志。最终的知识转化为体验。”[9]“敬畏生命是我的生命意志的最直接的和最深刻的作为。在敬畏生命中,我的认识变成体验。”[10]由此可见,施韦泽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以认识归结为体验、理性主义归结为神秘主义为基本线索,把歌德的“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思想与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生命哲学结合了起来,从生命的角度理解自然和世界整体,强调世界观和生命观问题就是我的生命意志对待本身和其他生命意志的行为问题,阐明了其“生命自然哲学”的基本内涵,实现了西方哲学现代性认识论向后现代性的生命哲学之思想转变,并由此说明,自己的敬畏生命道德原则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直觉或者道德情感,毋宁说,它也是有其深刻的哲学论证基础的。
施韦泽对欧洲思想直到近代仍然还不能够使同情适用于动物的生命而深感遗憾,对中国伦理思想从来都没有像沦为枯燥的实现个人和社会福祉说教的欧洲伦理那样面临过危机,而是始终与自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坚持伦理思想向道德行为的转化并不只取决于个人社会归属的权衡,而是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注重个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思想,十分赞赏和高度推崇。在关于欧洲哲学和中国哲学对于自然态度的比较中,他特别强调中国古代思想认为自然是神秘莫测的,对自然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只敢于理解它在生存中必要的那一部分”,而“对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欧洲哲学则致力于认识在自然现象中起作用的规律”,不仅敏锐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生态意义,而且也对欧洲的自然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施韦泽阐发“生命自然哲学”,不仅是为了克服欧洲思想始终把道德限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缺陷,而且也是为了克服其只在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思考道德问题和进行道德追求的局限。就施韦泽这两种努力的典型表述而言,如果说,前者体现为已被我国学界比较熟悉的“敬畏生命”原则;那么,后者则体现为还使人比较陌生的“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观念。虽然“敬畏生命”和“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这两个命题互为表里,就其伦理贡献和社会影响而言,“敬畏生命”原则甚至还更大和更为典型;但我们同时也应该十分重视“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因为它不仅是敬畏生命的哲学论证基础,把握了它也就易于理解其“生命自然哲学”,而且由此也有利于我们理解其向东方伦理思想的靠拢:不满意欧洲思想“把伦理限制为调控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之局限,而是要“把伦理理解为个人对宇宙行为的意愿”。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和观念,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就不仅是一般的生命伦理学,并且还具有了强烈的和直接的生态性。因此,施韦泽之所以被西方思想家公认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主要先驱之一,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当代中国学界,特别是生态伦理学和环境哲学界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可以说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对中国古代“人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思想的高度重视和深刻阐发密不可分的。总之,“人应当努力追求使自己的行为同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保持一致”,“只有通过伦理的行为人们才可以达到和世界相一致的境界”,“世界只有在有道德的人出现的前提下才能变得美好而有意义”,施韦泽所发挥的这些中国古代哲学命题,不仅敏锐地揭示了中国思想“天人合一”的特质,而且也深刻地印证了其本人“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的命题,以至整个“生命自然哲学”具有高度的生态伦理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施韦泽的这些发挥,正值中国发生了“打孔家店”的时代,现在看来就显得特别可贵。
在提出施韦泽要求“把伦理理解为个人对宇宙行为的意愿”,指出其不仅敏锐地揭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天人合一”的特质,而且也深刻地印证了其“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命题具有高度的生态伦理性之后,就有必要比较一下其“生命自然哲学”与中国古代思想的关系了。一般说来,施韦泽的“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命题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都强调人与无限的自然建立精神和道德关系,都把生命理解为自然、世界和宇宙的本质,并且都把爱惜生命和敬畏生命作为最根本的伦理要求。就此而言,两者有相当的类似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必须指出的是,施韦泽的生命自然哲学与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又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古代思想主张“天地之大德曰生”的道德价值,还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论证方式。施韦泽赞成“生”的道德价值,却不认同“天地之大德”的论证方式,认为这种论证建立在“对世界简单解释的基础上”,是“从伦理上简单解释世界意志”,从而是一种世界观念和生命观念的一元论及泛神论的世界观,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认为世界的根源是伦理的?在我们的生命意志对这一根源的奉献中,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伦理的?例如,基于同样的论证方法,在老子和庄子那里,行动伦理几乎丧失殆尽;而在孔子和孟子那里,行动伦理尽管在努力坚持自己,但也走不了多远。据此,施韦泽主张世界观念和生命观念的二元论。所谓世界观念和生命观念的二元论,实际上为自然律和道德律的二元论,指自然是一种“神秘的、充满痛苦的过程”,它既最有意义地产生着生命,又毫无意义地毁灭着生命。在这一过程中,生命以其他生命为代价才得以生存下来,其中只有人才能够敬畏生命。因此,人们不可能把道德的根据建立在自然之中,而是必须把自己生命意志的体验作为道德的源泉。用施韦泽本人的话来说,即“我的认识是悲观主义的,但我的意志和希望是乐观主义的”[11]。通过敬畏生命的意志,人与宇宙建立了精神关系,也与无限者建立了精神关系,从而也就确立了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道德原则。这里,笔者暂不展开对施韦泽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及其论证方式的评价,而是首先分析,施韦泽这么做,并由此表明的其“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以至整个“生命自然哲学”本身的特质何在?
简要地说,“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首先不同于欧洲近代以人作为主体、以自然作为客体的主客二分哲学,是一种倡导人与自然合一的“天人合一”哲学。这种“天人合一”哲学与中国古代的生态伦理思想有着很大的类似性,即都与人类的农业活动有关;这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施韦泽对中国哲学和歌德自然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中。但不同在于,施韦泽的“人与自然合一”思想是接受过西方近现代科学及其主体性哲学洗礼的,而中国古代思想则缺乏强烈的主客二分追求,也没有发展出近现代西方型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应用。其次,“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是一种生命哲学,它从人类个体的生命意志出发理解自然、世界、宇宙,面对自然创造和毁灭生命的二元性,扩展了西方的道德义务概念,强调个体要对一切生命承担起责任;这方面的思想既吸取了印度和中国思想的成果,又与施韦泽继承和发展叔本华和尼采的生命哲学有关,而与中国古代思想从“天地人”的生命整体息息相关出发,强调人的道德责任的论证方法差别较大。再次,作为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在他看来,“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也与上帝相关。尽管施韦泽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基督教神学家,但即使他也不可能否认上帝的存在。施韦泽认为在自然、世界和宇宙之中,上帝显示为造物主意志,这是一个完全神秘和令人痛苦的谜;在人心中,他则显示为爱的意志:“我们只有通过爱才能和上帝成为一个整体。一切对上帝的有活力的认识都归结于我们在心中体验到上帝是爱的意志”,[12]因此,“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也就是与上帝合一;这方面的思想是施韦泽独特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深刻体现,同时也正是现代新儒家徐复观批评施韦泽的地方。当然,对于这一批评,我们必须进行慎重的解读。总之,通过其世界观念和生命观念二元论的论证方法,通过“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命题对“敬畏生命”道德原则的论证、补充和深化,施韦泽明确了道德的根基在于人心,在于“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心”,不仅在道德论证形式演进的意义上,体现了人类道德自觉性的提高和深化,而且也使其生命自然哲学不同于西方其他类型的生命哲学,具有强烈的、直接的生态性,与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接近。此外,由于它既吸取了近代科学及其主体性哲学的成就,又与基督教的博爱伦理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样就更使它成为一种包含着中国古代伦理所不具备因素的现代西方伦理思想。由此可以说,施韦泽的生命自然哲学确实是西方哲学和伦理思想的突破,是东西方伦理思想的融合,对于推进人类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的进步,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同时由于其倡导者的身体力行,更强化了其实际的影响力。
四、 中国思想的伟大功绩
在对敬畏生命思想时代意义的探讨中,与人生观的道德个人主义、文化观的文化伦理主义、世界观的生命自然哲学等方面相比,施韦泽对中国思想伟大功绩的明确,由于其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直接相关,以及与当代中国人尚未完全澄清的文化自我的明显对照,从而是最令中国读者感兴趣,也是最值得中国学术界加以探讨的问题。施韦泽对中国思想的,时间跨度为自三千余年前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思想之诞生开始,直至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思想发生危机和面临转折为止,不仅简练地概括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系统线索,而且对中国思想的特质、贡献、局限、前景等问题也发挥了十分独特而又深刻的见解,成为当代中国人自身反思文化进程、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觉、立足文化振兴、实现文化复兴的一种宝贵的域外参考文献。特别是由于施韦泽对中国思想伟大功绩的相关论述,最近才被翻译成中文,是一种新的资料,还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因此,在上述“中国研究”篇中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分析之后,笔者觉得更有必要和责任对其所包含的重大启示意义作进一步的发挥,以供学术界和相关读者参考。就内涵和地位而言,施韦泽对中国思想的,首先体现在其作为一个有着充分“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对中国思想极高的评价之中:
中国伦理是人类思想的一大重要功绩。较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中国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它个将伦理视为一种以绝对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精神本质中的东西,它也是个从其基本原则中发展伦理思想,并且个提出了人道理想、伦理文化理想——并且以一种适应任何时代的方式。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伦理思想,中国伦理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它以自然而细致的方式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13]
中国伦理思想千百年来对于个人和全民族的教育的功绩是伟大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有这样一个建筑在伦理思想之上的文化来与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的相匹敌。欧洲思想中——由于基督教的关系——也存在理想的典型,但它没有像中国思想那样在一个持续的、繁荣的和精致的文化中得以实现。[14]
由于这两段评价可以视作施韦泽关于中国思想伟大功绩的经典表述,因此这里再次引证并在注释中附上德文版原文,以供有兴趣的研究者深入把握。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在对整个人类思想和宗教,包括中国思想及其宗教性,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查拉图斯特拉的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以及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思想的比较中,除了对启蒙运动有些加以单独探讨的必要之外,可以说,施韦泽对中国思想的评价是最高的。这种高度评价对于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赶超西方,直到现在才有所眉目的中国、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思想界来说,似乎不仅有点出乎意料,使人有点不敢接受,而且也使人产生疑问:施韦泽这么高度地评价中国思想,有没有理性的论证?是否只是出于一种个人的特殊偏好和情感投射?对此,笔者的回答是明确和坚定的,他对中国思想的高度评价与其说是个人的特殊偏好和情感投射,毋宁说是一种具有高瞻远瞩的人类思想史视野和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比较的理性论证。施韦泽认为中国思想和伦理的基本内涵包括:在人的精神和道德本质中确定伦理的根源,基于“人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的基本原则发展伦理思想,提出了普遍的人道理想和文化理想,在世界主义的文化人类理想的基础上,坚持“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并要求人们按照道德原则合理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争取文化的全面和真正进步,等等。正是在此概括的基础上,施韦泽可以坚定地确认,“中国伦理思想千百年来对于个人和全民族的教育的功绩是伟大的”。比自己所属的西方世俗文化,甚至比自己直接所属的基督教文化的功绩还要伟大。此外,如果说以上对中国思想的还是在广义文化比较基础上进行的话;那么,施韦泽还有对中国文化严格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和评价。这方面的内容,在笔者关于施韦泽考察东方思想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思想和哲学的总体评价、对中国伦理思想的特殊关注等问题的探讨中已经有所揭示。施韦泽认为,就实质性的价值观念而言,中国思想实际上已经是一种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包含着追求内在和外在文化的强大动力,和他本人要所追求的“敬畏生命”世界观高度一致;并对其“只有通过伦理的行为人们才可以达到和世界相一致的境界”的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和生态哲学,对其“人对任何人都负有义务”的人道观念和政治哲学,对其“让伦理存在于对一切造物的善意行为之中”的生命哲学,对老子“兵者,不祥之器”的和平信念,对庄子“桔槔”中的机械文明批判等思想,都予以了深入的解读和自觉的汲取,并由此也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传统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
就具体的思想学派而言,在施韦泽对中国思想的中,除了对“作为一种执对生命和世界肯定观的神秘主义和一种超脱于世俗伦理的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观”之道家思想的独到评价之外:“《道德经》是一本永恒的巨著”,“康德和黑格尔是欧洲思想的大师,老子则是人类思想的大师”;对于当代中国思想发展更具启示意义的则是他对中国伦理思想历史命运的关注,特别是他对孔子和儒学与中国未来思想之关系的探讨。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由于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竞争和压力,由于欧洲和美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的影响和渗透,为救亡图存,中国也进行了自军事装备、生产经营以至政治改革和暴力革命的努力。进入20世纪,思想文化的变革也风起云涌,在“五四运动”之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逐步走上了与传统思想实现彻底决裂的激进道路,抛弃传统思想的一切,特别是“打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直至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批孔”运动中达到极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普遍进步,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其中作为进步标志之一的就是传统思想和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和文化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大量儒家经典及其研究和解读著作被出版,各种儒家学术研究、教学和传播机构纷纷成立,儒学讲座和儿童、青少年诵读活动等更有遍地开花的趋势,以儒学为核心和代表的传统文化正在逐步寻找自己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之中。但是,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复兴。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就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复兴。因为任何一种离开和断裂自己文化根基的民族,或者是没有生命力的,或者干脆就丧失了自身的文化身份,成为了另外一种民族。而从这一要求来看,我们就必须承认,当前所谓的“国学热”和“儒学热”实在是初步的,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无论从思想观念和建构方面来说,还面临着极为复杂的问题,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才能够建立起一种儒家思想有着其合理位置的文化和道德结构,以延续先前五千年以上的文化生命,并走向更加美好、和谐与伦理的未来。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再来看施韦泽关于“尽管与潮流不相一致,但未来依然属于孔子”的论述,难道不能够从中获得必要的启示吗?
由孔子一手创造的思想还没有达到它最完全的发挥……如果设想一下中国思想的明天,那么它必然是一个从孔子学说出发的通过实现其开始具有的各种可能性并将其中蕴含的所有生机和活力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的有所革新的思想。……对孔子精神做符合时代精神的革新意味着精神和伦理文化对于物质主义文化的一次胜利,它将不仅对于中国,甚至对于全世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15]
面对这样的论述,基于当代中国思想界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近现代中国命运的反思,我们必须承认其关于中国思想的确实是当代中国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觉、立足文化振兴、实现文化复兴的一种宝贵参考,值得学术界和文化界予以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当然,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要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以至于整个人类社会中发挥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功能,自身也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果断地扬弃自身文化中的过时和消极因素,自觉吸取其他文化、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以成为一种既适应时代要求、又能够引领时代精神的新儒学。而在此,施韦泽的相关论述也值得我们思考。例如,在他看来,经济方面的地主剥削农民、农业生产停滞、人口爆炸和民众贫困等问题的存在,“表明了孔子思想本身蕴含着的悲剧式的无能为力”,说明儒学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确实需要吸取近现代西方的积极成果。此外,施韦泽坚持西方启蒙运动的人道和人权思想,特别倡导“每个人应该在尽可能合乎人类尊严的生存条件下达到真正的人性”,“人从来不应该作为祭品而牺牲于现实状况”,而对近现代西方具体的政治制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强调,这一切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与时俱进也是一种启示。以上属于实践方面,至于在理论上的局限,在《生命自然哲学》一节中,笔者已经阐发了施韦泽对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以“天地之大德”为基础论证“生”的道德原则的方式的批评,即“从伦理上简单解释世界意志”的批评,尽管可以探讨;因为在“最终价值是不可论证的”当代世界,任何最终价值的确立实际上都与一定的社群相联系,与特定的论证方式相联系,都不能随意地强加于人,但必须承认,他的批评毕竟是现代新儒学必须加以澄清的一个基本问题。当然,这绝不是说,任何价值都是相对的,都具有同等价值。事实上,作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类道德共识,“天地之大德曰生”中的“生”,与“敬畏生命”一样,都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道德原则。因此,考虑施韦泽对中国思想局限的批评问题,应该集中于中国伦理的自然与伦理相和谐的一元论的“局限”。
所谓中国伦理的自然与伦理一元论的“局限”,在施韦泽看来,首先指在“战斗的精神”上,中国伦理缺乏持自然和伦理二元论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那种伦理,存在着一种出于对现实中的奥秘的敬畏的认同。确实,就认为自然是一种“神秘的、充满痛苦的过程”而言,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世界中的痛苦之认识和体验不如基督教,人生的悲剧意识不强,对“生”之根源的“天地”抱有一种“乐天知命”的情感,有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理,导致突破现实的强度不够,尽管由此也避免了基督教扩张性的自我中心主义。对于这一点,思想史家韦政通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儒家毕竟“不能使历史产生里程碑式的变化”[16]。从而中国思想在这方面可以向基督教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双方的互补。其次,施韦泽认为,中国伦理虽然提出了人的伦理理想,但还是局限在自然人伦的关系之内,对基督教强调的诸如对于不公平的忍受、不加限制的宽恕、施加于敌人的爱等等,都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但笔者认为这方面的不同,虽然也有理论上的根源,但更重要的则是实践上的差别。因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伦理发生于宗法封建社会,还没有完全剪断自然血缘的纽带;而基督教伦理则出现于古罗马的世界帝国,只有摆脱了血缘、民族的羁绊才可能生存和发展。从而,儒家和基督教之间这种差别主要是历史地形成的,也可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当然,“如何不是将理想局限于在人类社会中实现完善的自然秩序,而是在最高的行为上去认识爱的思想,是中国伦理必然面临的挑战”,施韦泽提出的这一问题,还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如何既摆脱血缘性的自然关系的局限,发展出类似基督教的博爱伦理,同时又通过自己的伦理行为达到与天地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无疑是当代中国思想和伦理必须致力解决的问题。在此,施韦泽也认为,首先应该考虑尽可能完全保持与自然哲学的联系。对于他的这一“生命自然哲学”观点,笔者也是赞同的,并认为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中国伦理思想反过来也会给予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整个西方伦理以积极的影响。总之,以上是笔者对施韦泽中国伦理局限论的初步分析,不可能提出什么有深度的见解。但鉴于此问题在中西伦理比较中的重要性,因此抛砖引玉,寄希望于大方之家的关注,并由此也促进中国学术界对施韦泽生平和思想的研究。
另外,关于施韦泽对“中国思想的伟大功绩”的评价,如果参照一下现代瑞士著名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的《黑塞之中国》(德文原书名为China, Weisheit des Ostens,直译应为《中国——东方的智慧》)一书,也许会进一步有助于我们对其意义的理解。黑塞与施韦泽生活的年月几乎相似,同样在中华民族面对东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最黑暗时代,不仅对中国文化表示了由衷的赞赏,而且认为孔子的《论语》“迫使我们用另一种眼光审视我们的个人主义文化,以其相反面比较,不再把它看成那么自然而然”[17]。黑塞是于1911年首次接触中国人的。当时,黑塞次到东南亚旅行,看到了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和黑人,等等,其中给他留下“最初最深刻的外在印象是中国人”,“对中国人从一开始我们就得到一种印象,知道这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知道自己的文化并不后顾,而是在行动中向前看”[18],激发了他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面对列强对中国侵略压迫,黑塞认为:
作为民族,中国人落后于我们的是文明的外在完善,也就是机器与大炮之类的东西,但我们不能以此去衡量文化。即使这些东西,中国人在几百年前也走在我们前面,他们也比我们先发明火药和纸币。在这些领域他们被我们超越了,现在依靠我们了,但他们文化的根源并未被超越,目前,文化虽然处于危机之际,但远不至于伤筋动骨。中国文化的根源和我们当前的文化理念正相反,我们应该乐于见到在地球的另一半存在着一个坚固而值得尊敬的反极。如果有人希望全世界都奉行欧洲文化或者中国文化,那会是一种愚蠢的想法。我们应当学习这外来的思想,把东亚也看为我们的老师,就像我们几百年来把近东看作老师。[19]
展现了一种深刻的世界主义文化眼光,既不取西方文化中心论,也不盲目崇拜中国文化,而是“更加坚定地相信文化的国际性能力”,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积极综合。更值得注意的是,针对20世纪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出现的对传统文化“全盘西化”和“彻底决裂”的思潮,老年时期的黑塞除了表示惋惜和忧虑之外,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仍然保持着充分的信心:“如果我们拿十七世纪的英国、法国来与之比较,就可以看出,几百年的过程中,一个在政治方面会有极为重大的改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民族性的核心也会有相应的改变。我们愿望,中国人民越过这段混乱困惑的时期,保持住他们美好的特质和天赋。”[20]虽然黑塞的看法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终生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保持的“善意”和“敬意”,还是值得正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们予以充分的重视。注释:
[1] 钱穆:《晚学盲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3] 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页。
[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4页。
[5] 同上书,第3694页。
[6] 关于施韦泽的文化伦理主义,实际上,我国文化哲学家陈经序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所阐述。在《文化学概观》(岳麓书社2010年版)一书中,陈经序把施韦泽(什维兹尔)视作欧洲人“以道德的立场,去解释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概括分析了《文化哲学》的基本观点。当然,对于他在书中把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解为“生活的敬仰”,我们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7] 陈泽环:《道德结构与伦理学——当代实践哲学的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另参阅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 关于此处对施韦泽与海德格尔之思想的比较,可参阅日本哲学家本田元《反哲学入门》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9] 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10] 同上书,第107页。
[11] 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12] 同上书,第135页。
[13] 阿尔伯特·史怀哲(施韦泽):《中国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译文有改动)德文版原文为:Die chinesische Ethik bedeutet eine grossartige Leistung im Denken der Menschheit. Allem andern Denken ist das chinesische darin voraus, dass es als erstes die Ethik als etwas in absoluter Weise in dem geistigen Wesen des Menschen Begruendetes schaut, als erstes die Ethik aus ihrem Grundprinzip entwickelt und als erstes das Humanitaetsideal und das Ideal des ethischen Kulturstaatsund dies in einer fuer alle Zeiten gueltigen Weiseaufstellt. Als hochentwickelte Ethik zeigt sich die chinesische auch darin, dass sie hohe Forderungen hinsichtlich des Verhaltens von Mensch zu Mensch vertritt und dem Gebote der Liebe eine auf alle Wesen gehende Bedeutung gibt. Diese Vorzuege und Errungenschaften kommen noch dadurch zu bester Geltung, dass sie auf Grund ihrer Lebensund Weltbejahung gesund ist und sich in natuerlicher und eingehender Weise mit den Tatsachen der Wirklichkeit auseinandersetzt.
[14] 同上书,第104—105页。(译文有改动)德文版原文为:Was die chinesische Ethik durch die Jahrhunderte hindurch in der Erziehung der Einzelnen und der Voelker geleistet hat, ist grossartig. Nirgends auf der Welt hat es eine auf ethischen Ideen beruhende Kultur gegeben, die sich mit der auf dem Boden Chinas bestehenden messen kann. Wohl besitzt auch das europaerische Denkendurch das Christentumhohe Ideale.Aber es kann nicht dazu, sie, wie das chinesische, in einer stetigen, gediegenen und feinen Kultur zu verwirlichen.
[15] 同上书,第107页。
[16]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7] 赫尔曼·黑塞:《黑塞之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17页。
[18] 同上书,第97页。
[19] 同上书,第92—93页。
[20] 同上书,第1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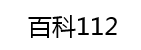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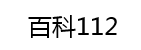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悟空大厅怎么开挂”(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悟空大厅怎么开挂”(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