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著作相比,《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稍显特别。本书是部系统阐述中国流氓问题的专著,在书中,作者就流氓的起源及变迁作了详尽的叙述,将中国历史上流氓这一社会阶层的生活状态、形象以及与社会的关系系统勾勒。
正如人们所习见的那样,在两千多年里,流氓意识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而流氓的历史也必然会影响法治、道德、文化等诸多方面。就流氓的产生演变,流氓习气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等问题,我们的特约记者采访了陈宝良。
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明史。著有《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的社与会》《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等多部专著,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明清史论文百余篇。所著多被海内外知名大学列为学生指定参考书。其中《中国流氓史》《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两书,已被翻译成韩文、英文出版;《明代社会生活史》一书,则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4年度十大社科图书”,并入围“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
中国历史上的流氓
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新京报:王学泰先生以研究游民文化著称,他强调,“游民”跟“流氓”不能画等号,古代的“流”和“游”差不太多,“民”和“氓”也相通,“游民”和“流氓”这两个词并没有本质区别,但现在“流氓”这个词发生演变非常大,特别是现在讲到流氓学等等,并且讲到“流氓”这个词有贬斥的意思。王先生对游民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评价,并没有贬斥,游民的产生和演变,他们在社会上起正面或负面的这种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思想和想法的复杂,而是社会演变的结果。
《大明风华》390-400页写到了明代的流氓,《无籍之徒》是一部研究中国流氓的专著,你强调,流氓属于游民(600页)。在你看来,流氓和游民的区别在哪里?
陈宝良: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无籍之徒》这本书的写作原委与出版过程做一个简单的交代。这并非自己“王婆卖瓜”,而是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一论题的学术意义,进而同情地理解作者写作此书的用意乃至苦衷。
《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增修版)》,作者:陈宝良,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
拙著最初名为《中国流氓史》,199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首印万册,在当时算得上是学术畅销书,这是我聊以欣慰的事情。此书先是被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且翻译者凭借此书获得2001年度韩国“中语中文学会翻译奖”。记得当年在韩国获此大奖的有两本书,另外一本是《鲁迅》一书的译者。这应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鲁迅是我的同乡先贤,我之所以写作此书,除了个人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之外,实际上更多地是受到了鲁迅《流氓的变迁》这一讲演稿的影响。此书韩文版出版后,韩国《东亚日报》《朝鲜日报》《每日新闻》《京乡新闻》均有书评与书讯。至于有关拙著的书评,更是见诸中国大陆之《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博览群书》《中国史研究动态》,香港之《大公报》,日本之《明代史研究》,法国之《汉学文献评论》等报刊。
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所敬仰的著名汉学家卜正明教授亲自为拙著撰写了书评,在法国的《汉学文献评论》上刊发,并在他所写的汉学名著《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此书获2000年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中,将此书列入参考书。另外,美国汉学家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教授在其所著《中国历史手册》(Chinese History : A Manual)一书中,也对拙著有所评价,使此书得以成为哈佛大学学生研究汉学的参考书,这也是令我鼓舞的好消息。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拙著再版,并于2013年又修订出版。
这次再次增修,改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易名为《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改用“无籍之徒”一名,会更符合历史的实际,即从社会史的视角来看,流氓确实是脱离了户籍制度管理的游手好闲之徒,甚至成为一种“弃民”。
回到问题上来。关于“流氓”与“游民”的区别,我基本上同意王学泰先生的看法。事实上,我在书中的基本观点,大致也与王先生的观点相同。为了使这种区别得以更加明晰,我在这里不妨做进一步的申述。简单地说,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流氓也是游民,是游民群体中的一个分层;二是并非所有的游民均可以归属为流氓,因为维持生计的手段与行为的特殊性,导致流氓在游民群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如果更为详细地说,游民是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游离出来,且不工、不农、不商、不士的独立于“四民”之外的社会群体。从传统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举凡“不事恒业者”,均可视为“游民”。可见,游民概念的内涵,确实比“流氓无产者”更大一些。流氓,尤其是职业流氓,既来自流民,更来自游民,是一批专事游荡、扰乱社会秩序、为非作歹的不良莠民。尽管流民也是产生流氓的“后备军”,但从总体上说,史学界对流民有一个基本的涵义界定,他们大多为一些安分守己的饥民,最为急迫需要的还是追求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即土地与粮食。一旦有可能,他们会重返家园,附着于土地之上,重新登录于户籍之中,即使不再回到故乡,同样也会以“附籍”“客籍”等形式,登载于寄居地。从广义上讲,游民也是流氓,他们与流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游民这一概念明显大于流氓。换句话说,游民除了流氓,以及一部分职业性的盗匪之外,还包括游丐、江湖卖艺者、习拳舞棒者、赌徒、游方僧道、散兵游勇等。
明 周臣《流民图》。
新京报:流氓的产生和演变又具有怎样的特征?
陈宝良:追溯流氓的源头,反而是游士与游侠成为了流氓的祖师爷,而并非后来的职业游手。鲁迅认为,流氓一来源于“孔子之徒,就是儒”,二来源于“墨子之徒,就是侠”。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见解。孔子之徒,儒家的末流,即战国时期的“游士”,他们不仅具有“儒的诡辩”,而且颇有些流氓习气。在战国时期,这些游士又被称为纵横捭阖的“策士”。他们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人主,议论古今,陈说利害,上为排解忧患,下为自己博取富贵,可见不过是一群寄食于君主门下的政治流氓。当然,先秦贵族政治崩溃之后,失去世业的流民,并非仅仅限于这些作为孔子之徒的“士”,其实还包括原业农工的下层失业流民,这些人大多成为侠士。其中的墨家,多出自这些侠士。尤其是墨家中的“钜子”,更是成了后世黑社会的嚆矢。
流氓在后世的演变,大抵沿着这两大群体展开:归于儒家的“士”,在上进正途无门的窘境下,转而堕落为一些“帮闲流氓”,诸如先秦时期的“门客”,唐代的“妙客”,以及明清的“山人”“清客”,均属于此类流氓;归于墨家的“侠”,在战国、汉代一度很盛行,转而流变为秦汉的“闾巷少年”,魏晋南北朝的“无赖少年”,隋唐的“坊市恶少”,以及明代的“打手”与“打行”。当然,流氓的源头并非仅仅限于儒、墨的末流,更多的还是游离于土地的职业游民。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惰民”与“闲民”,唐代有了“闲子”,宋代有了“浮浪人”与“闲人”,元代有了“无徒”与“无籍之徒”,明代有了“逸民”“喇唬”“光棍”与“把棍”,清代有了各色“棍徒”,更是名目繁多。诸如此类的特殊群体,才称得上是流氓演变中的生力军。
至于流氓演变的特征,基本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儒、墨之徒的日渐堕落。儒家之徒的堕落,尤其是士行的无赖化,应该说是知识阶层的最大悲剧。原本应该凭借自己的知识,积极投身于治国平天下的千秋功业之中,但最后因为上升途径的狭窄,导致诸多士人的“失业”,成为了“失职之士”,不得不沦落为凭知识依附于权贵大佬之门的门客与帮闲,甚至不乏做出一些捧屁、呵大卵孵的丑陋行径来。这无疑是值得后来的研究者最为值得深思的事情。墨家之徒的堕落,甚至侠客失去原本正面的形象,同样值得引起关注。流氓是侠客堕落以后的产物。换句话说,真正意义上的侠客、剑侠一流人物,理应是秉天地之正气,能为人雪不平之事,霜锋怒吼,雨血横飞,最称得上是世间快人,可以行世间快事。
可惜的是,后世所谓的侠客,已经很少得此真传。世人偶然学得几路拳脚,舞得几路刀枪,便俨然自命为侠客,不是贻祸身家,便是行同盗贼,最后还是把一个“侠”字弄坏了。这就是说,后世的侠客,已经堕落成“以杀人为好汉”,或者“借放纵为任侠”。二是职业流氓的崛起。时至明代,出现了“喇唬”“光棍”这两个专有称谓,均属于专门害人的“之匪”,也就是职业流氓。到了清末,“流氓”这一称谓更是出现了转化,即从原本泛指流民的称谓,转而成为职业游手的称谓。这一称谓,不仅见诸当时的报纸《申报》上,甚至见于官方的史籍即《清实录》上。
新京报: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都曾经是流氓,他们也都完成了从流氓到皇帝的人生逆袭。一般说来,从最底层崛起的皇帝和官员,对权力会看得特别重,甚至有一种畸形的迷恋。而这两人也正是如此:刘邦称帝以后,以种种借口翦除异姓王,同时又分封刘氏子侄为同姓王;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持续时间有十几年;刘邦生前与群臣定下白马之盟,立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约,以此作为巩固西汉中央政权的辅助手段。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将权力空前集中。那么,两人身上的流氓习气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种流氓习气对于两朝的政治文化乃至社会风气的塑造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陈宝良:正如台湾学者萨孟武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对传统社会最高统治者构成极大威胁的不外乎下面两类人:一类是地方豪强,如曹操、杨坚、李世民之流;另一类是流氓,即被统治者斥责为“乱民”的那批人,如刘邦、朱元璋之流。大致说来,地方豪强有财有势,平时积累财富,招纳亡命,聚集门客,一旦社会动荡,他们就起兵夺权,便于成功。这自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流氓光棍一条,一无所有,了无牵挂,所以能做到勇于冒险,无所顾忌。尽管历史上流氓争夺帝位的斗争频繁发生,但其成功者寥寥无几。当然,争夺帝位的野心,却是这些流氓人人具备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尽管豪强与流氓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与社会阶层,他们的行为却颇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豪强需要流氓,流氓也离不开豪强。他们臭味相投,虽不可能结成永久性的联盟,却也能一时狼狈为奸。流氓一旦依附于豪强,其违法活动就会得到庇护,得以逃避法律的惩罚;而豪强如果得到流氓的支持,就会在原有财势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泼皮的胆气与手段,从而在政治角逐中所向披靡。
刘邦、朱元璋堪称中国历史上政治流氓的典范。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少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无赖,不能治产业”。至于朱元璋的出身,有人认为是“游丐”,有人认为是“游方僧人”。其实,自宋代以后,所谓的游方僧人,大致与游丐相近,一概被称为“挂褡僧”或“挂单僧”,均属于游民。清代史家赵翼曾称明太祖朱元璋其人,一人兼具圣贤、豪杰、盗贼之性,这显示出相当敏锐的史识。
电视剧《楚汉骄雄》剧照。
政治流氓最为显著的本性,就是不讲信义,翻脸不认账,心狠手辣。举例来说,凡是手下将领在战场上失利,就会被违纪斩决,但到战争胜利后,政治流氓又会反过来大举杀戮有功战将,其理由无非是犯了功高震主的忌讳。可见,屠杀、迫害功臣宿将,是政治流氓本性的大暴露。如刘邦就杀了韩信、彭越,而朱元璋则先后制造胡惟庸、蓝玉惨案,胡案族诛至三万余人,蓝玉案也诛至一万五千余人,开国功臣几乎一网打尽。所以,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至理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另外,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太平原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这两句话,一方面说明凡是参与创业的功臣武将,他们在建国以后尽管也会享受到短暂的富贵荣华,但终究无法荣耀终身,甚至不乏被诛戮的悲惨下场;另一方面,又告诫那些功臣,在面对流氓皇帝春风得意之时,应该及时避其锋芒,尽早隐退,以免成为皇帝的案上之肉。当然,这种事情不仅发生在君臣之间,有时连骨肉之间也是如此。而刘邦、朱元璋所行之事,就是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脚。
当然,皇帝出身流氓,或者说皇帝天生带有一些流氓习气,其中对于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可以从好的或恶的两个层面加以考察。从好的层面来说,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一段经历,显然使皇帝可以洞彻社会下层的疾苦,一旦登基成为皇帝,那么在颁布或实施的政策中,会出现一些同情小农或社会底层的政策,也就是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这些政策,固然是为了自己的江山的安定乃至万年长久,但确实对于王朝建立初期社会经济恢复乃至民众生活的改善不无裨益。这无疑与他们自己的那段经历不无关系。从恶的层面来说,皇帝出身流氓的经历,对于一代政治风俗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例,其超越制度乃至法律的强权行为,至少在当时的政治层面已经留下了不好的恶习:一是唯我独尊,一方面是制度的建设者,另一方面又是制度的破坏者,《大诰》《大诰武臣》的颁布,足以证明皇帝的权力可以超出制度之外,甚至凌驾于一代典制的《大明律》之上。除此之外,洪武时期为具体处理胡惟庸、蓝玉二案而独自颁布的《昭示奸党录》与《逆臣录》,同样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流氓出身的皇帝可以为了一己私利而大肆杀戮功臣,并藉此警示甚至恐吓臣民。二是独断专行的行政作风,显然已对从元末过来的知识人产生了心理警示的作用,明初知识人不愿意进入地方学校成为秀才,或者说一些知识人不愿意出来做官,就是典型的证据。至于对社会风俗的影响,鉴于相关证据的缺乏,很难在这里一一展开阐述。
电视剧《洪武大案》剧照。
明代流氓与一条鞭法
新京报:《无籍之徒》185页写到了万历年间北京的流氓——以锦衣卫官员韩朝臣为首的“十虎”。“十虎”与苏州的流氓“龙蛇帮”并称万历时期的“双黑帮”。有人认为,万历时期是黑恶势力最猖獗的时期,几乎每个城市都有黑帮存在,而黑帮的出现,则与“一条鞭法”导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高度相关。对此,你怎么看?
陈宝良:若以明代社会、文化、生活、风俗等为视角,相对重要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应该说是在成化、弘治年间。更确切地说,发生在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时期。正德前后,明代的社会、文化、生活、风俗发生了前后大为不同的变化,而并非需要延宕至万历年间。
有意思的是,成化、弘治年间,是一个被后来的士大夫所百般称颂的时代,甚至可以与“三代”相媲美。但正是在这令人敬仰的两个朝代,流氓黑恶势力得以长足的发展。如果我们从《实录》与戴金编的《皇明条法事类纂》两种史料来看,成化、弘治年间,流氓势力至少发生了以下两大变化:一是新的流氓称谓“喇唬”的出现,他们的活动日渐猖獗。从当时的兵部尚书余子俊的上奏中不难发现,所谓的喇唬,实际上是指闾巷恶少与各处捕盗罪囚结聚党类之后的称呼。可见,喇唬既是一种流氓称谓,又是一种流氓团伙。二是出现了在当时颇为有名的流氓团伙。如成化六年(1470),山西太谷县的流氓头子杜文翥,自己号称“都太岁”,与兄弟一起结交一批恶少,号“十虎”“二贤”“八大王”等,暴横乡里,时常聚众做一些奸恶不法的事情。
当然,到了万历年间,流氓势力更为猖獗。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流氓团伙纷纷出现,并且靠结拜兄弟这种仪式维系团伙成员的关系,如当时北京的流氓头子韩朝臣,平日依靠锦衣卫的势力,结义十个兄弟,号称“十虎”,横行于京城各个地方。二是自万历以后,主要是泰昌元年(1620),在北京出现了“把棍”这样一种流氓称谓。这些把棍均为游手无赖之徒,平日主要靠“拿鹅头”(即讹诈愚笨之人)与“生事诈人”为业。“把”是把棍的团体。恶棍聚在一起,结成团体,就称“把”。我心中一直存有一个推测,这就是明代的把棍是近代四川“舵把子”的不祧之祖。
当然,这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目下限于资料的匮乏,尚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加以证实。三是“打行”的出现及其兴盛。明代中期以后,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松江两府,出现了一大批专职替人报私仇的无赖,这就是当时名震江南的“打手”,有时又称“青手”,而打手的则称为“打行”。在明清的史籍中,打行又称“打降”。这是因为,在吴语系统中,“降”可与“行”同音。所谓打行,就是以打人作为自己的职业。以松江府崇明县为例,万历年间的打行人员,比较著名的有曹铁、抄化、李三等人。天启初年,有杨麻、大陈、梅二、郁文、昌桥陈二、熊帽子等人。打行本身已经是一种流氓团体,但在此之外,他们又从中结成“团圆会”“地皇会”一类的。
晚明城市黑帮团伙的出现,固然少有直接证据证明与“一条鞭法”的实施有关系,但毋庸置疑的是,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大量流动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在明代,“一条鞭”有时又称“一条编”,原本是在明代久已存在的一种俗称,其中的含义具有简便、省心诸义,后用在地方赋役改革上,称之为“一条鞭法”。一条鞭的实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各地赋役改革尝试的结晶,而后至万历初年而广泛推行。据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至少至今没有资料证明,一条鞭法的实施,直接导致晚明流氓势力的勃兴。
不过,流氓势力与明代赋税徭役的关系,从打行这一可以得到部分的证据。这就是说,到了明代末年,打行的活动开始有所变化。当时由于官府追赋急迫,百姓无法按时交税,时常受到杖责之苦。于是流氓专门开设打行,实行垄断,代人挨板子。这些流氓替人挨板子,定有时价,一般每挨一板子付银二钱。此外,有一点倒是确凿无疑,即流氓势力是人口流动乃至社会流动的产物。进而言之,明代中期以后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显然为城市黑恶势力提供了温床。而大量人口流动的出现,无疑基于以下两个事实:一是明初所定官方户籍、路引制度的松弛,使人们有了外出、流动的基本自由,进而产生了诸多游手好闲的流动人口;二是官方管理僧道度牒制度的废弛,从而导致大量游方僧道的出现。
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剧照。
新京报:你此前的著作《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曾经写到,明代后期一些秀才堕落为流氓和无赖,《中国流氓史》271-275页写到晚明秀才被人雇作打手,以及秀才和流氓无赖结合,坑害普通民众。除了士风堕落的原因之外,这是否和当时读书人的出路太少,难以谋生相关?
陈宝良:秀才是一种民间俗称,正式的官称应该叫“儒学生员”。按照道理来说,秀才是斯文一脉,其行为不妨扭扭捏捏。所以,有人就把秀才形容为“处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大概从明代中期以后,士风开始堕落,秀才行为日渐无赖化,甚至如同“妓女”“淫妇”。这当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说的更确切一些,晚明的部分秀才,实则已经称为“劣衿”,甚至成为一个地方官必须面临的大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学蠹”。
晚明秀才的无赖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秀才一旦在科名上没有上进的出路,有些人就出任讼师,靠此维系家庭生计。尤其是到了冬末,一些原本在乡村教书糊口的秀才,都歇馆在家过年。一等有事,就终日缠官扰民,今日上手本,明日上呈子,兴讼、息讼,一由他们任意所为。他们包揽词讼,甚至成为“学霸”。这些劣衿的活动,犹如群宿的大雁,于是被人称为“雁”。百姓在路上遇到劣衿,就纷纷说:“雁来矣。”人人趋避,唯恐不及。秀才兴讼灭讼,甚至结成了“破靴党”。这个称谓很有意思,也很能说明问题。靴子是秀才的服色,代表着一种身份,非普通庶民可以穿着,但一个“破”字,足以说明秀才之穷,连一双崭新完整的靴子也买不起。
二是秀才闹事及其无赖化,甚至被称为“蓝袍大王”。所谓蓝袍,是秀才的服色,也就是青衿、襕衫。所谓大王,或指神庙中各色大王神像,或指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就是拦路抢劫的“强徒”,也就是落草为寇之人。秀才有“蓝袍大王”之号,无疑就是秀才无赖化的最好注脚。
三是晚明秀才多以“凶”出名。如当时苏州府常熟县有一位叫单君右的秀才,因凶相而有“鞑子”之号,里中百姓有“单鞑子倒凶”之说。到了明末,更是流传着这样的笑话:凡是市井闾阎中有人互相争斗,动辄曰:“我雇秀才打汝!”秀才本应温文尔雅,却被人雇去充当打手,一脸凶相。
至于士风堕落的原因,确实与士子科名之路日趋狭窄有关。当然,科举失败的秀才,虽然只能走不同于中举人、进士而后进入仕途那样的正途,但同样可以走岔路,以维持家庭的生计。这就是说,科举失败的秀才,并不一定会成为无赖流氓,在岔路中还是有两条路可走:大部分安分守己的秀才,通过教书、行医、入幕等正经职业而维持生计,其中一小部分不安分守己的秀才,则沦落为讼棍,甚至日趋无赖化。
《大明风华: 明朝人的城市生活》,作者: 陈宝良,岳麓书社 2023年1月。
流氓与官家权力
新京报:锦衣卫官员韩朝臣和其他9名流氓拜把子,成北京谈虎色变的流氓“十虎”,其他一些流氓的兴衰史都说明,城市中的流氓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勾结权力,撑起自己的保护伞。那么,在古代社会,流氓与政府权力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陈宝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流氓无疑是社会过剩的劳动阶级,也即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仅做不正规劳动的一股社会力量。而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来看,流氓是从农村土地中分离出来的一股社会闲散力量,是不事劳作或仅仅从事不正规劳作的职业游手。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流氓的起源颇早,而且在社会中的力量也相当强大。而流氓阶层力量的强弱,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传统小农经济的稳定与否。流氓一旦势力扩大,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势必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参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换句话说,流氓既有代表本阶层的政治与经济需求,同时也将积极地参与军事与文化活动。
流氓势力与权力勾结,渊源有自。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还是明清时期的清客帮闲,无不是寄食于衙署官员。此外,南宋杭州的“卖阙”,明代北京的“撞太岁”,也足以证明流氓广泛参与政治,积极充当政治上的说客与中间人,甚至不乏借用欺骗这种无赖的手段从中牟利。
至于古代社会中流氓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我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之:
其一,因为流氓势力本身对于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政府一直通过各种制度与法律手段加以积极的管理与惩治。从管理层面来看,就是通过登记造册制度,以便控制流动人口。尤其是像流氓这样的无籍之徒,更是将他们打入“另籍”“另册”,或者归入“弃民簿”,或者在保甲册中注明“游民”二字,以加强对这些黑恶势力的管理。从法律的层面来看,明清时期已经在官方法律中出现了对“喇唬”“光棍”这些流氓的惩治条例,以及相关的地方司法实践。
其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具体的历史事实中,确实不乏流氓与权力相勾结的例证。其中最为重要的例证,就是明清时期地方巡抚、巡按为了访察地方弊政与豪恶势力,不得不使用“采访”新闻的方法。而在巡抚、巡按采访的过程中,慢慢出现了“窝访”这样的弊端。换句话说,所谓的访察地方官员,更多的时候是被流氓“访行”所把持。如明代苏州府常熟县的访行“保生社”,其头目邵声施,被内的成员称为“大阿哥”。邵声施与当地的官员多有勾结,且往来频繁。于是,很多地方官员就成为邵声施等流氓成员的保护伞。
其三,官方的制度与法律,对于管理与惩治流氓势力固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然无法起到消除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真正效果。于是,在官员或士大夫中,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新见,即积极利用这些流氓势力并加以有效地管理。像“天罡”“地煞”“把棍”之类的流氓,无疑是一种“恶人”,也即良民的“蟊贼”。尽管所有官员与士大夫一致认同,只有去除这些“蟊贼”,良民才得以安居乐业。但在如何管理这些流氓的问题上,明末东林学者高攀龙则提出了颇为新颖的看法,即不再是除恶务尽,而是利用流氓中的首领,即那些所谓的“首恶”,由他们来管理与控制手下的党类。他的具体主张是将那些“天罡党”中的首领登记在册,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的薪禄,平时则由他们管束自己的成员,一有事情,再使用这些流氓。若是他们的党类中发生诈害良民之事,也是惟首领是问。这样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竟然出自以讲儒家正统之学为主的东林党魁之口,不能不说流氓无赖的势力在当时确实已是相当强大,以致儒家的正统人士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适当管理和利用好这些势力。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见解出自东林党人士,也将促使我们对东林党所代表的社会利益阶层作出诸多新的评价。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剧照。
新京报:《无籍之徒》317页写到了清代宗室人员的流氓化、无赖化,《大明风华》也写到了朱元璋的后代亲王、郡王、将军和流氓、无赖勾结。显然,这些“赵家人”(皇族)敢于作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享有特权,地方官不敢“违法必究”,因为君主制时代的中国是人治社会,享有特权者可以藐视法律。那么,地方官对此通常采取怎样的对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敢惩治这些“赵家人”?
陈宝良:宗室成员的构成相当复杂,其内部也处于日渐分化之中。换句话说,宗室成员也有上下层之分,上层宗室成员可以凭借自己的禄田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下层的宗室成员,尤其是那些没有名封的宗室“花生子女”,因为禄粮不多甚至没有禄粮而往往生计没有着落。至于宗室成员的行为,尤其是他们的无赖化行径,同样处于一种两分的状态:上层的宗室成员,则是把持地方衙门,武断乡曲,甚至广泛搜罗流氓无赖为自己所用;下层的宗室成员,则因衣食无着而游荡于社会,其行为几乎与无赖相同。
就此而论,宗室成员的无赖化,固然与他们本身享有的特权有关,但更是社会流动的自然结果。其实,以明代为例,朝廷对宗室犯罪的惩治同样具有一整套的法律体系,且在凤阳设立专门的监狱“高墙”,用来关押宗室中的犯罪人员。高墙的设立,一方面说明同样是法律惩治,宗室有着不同于普通民众的特权;另一方面,说明朝廷确实也在借助于法律而对宗室成员加以规范。尤其是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对自己的儿子诸如秦王等,一旦有了超越伦理与法律的不法行径,往往也会直斥其非,甚至不乏严厉的训斥,现在保存下来的《御制纪非录》一书,就是朱元璋记录自己儿子为非作歹行为的实录。
明代的宗室问题,有着一个内在的转向:在明初时期,宗室最大的问题是拥有护卫之兵,且权力颇大,进而对朝廷构成很大的威胁,而后才有建文帝的“削藩”之举,以及随之而来的“靖难之役”。朱棣获取皇帝宝座之后,同样实施的是“削藩”政策。可见,明初的宗室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王权与藩王权力的争斗。自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削藩”的成功,宗室一方面不再拥有护卫之兵,另一方面又被严厉禁止干涉政治,于是宗室只能埋首于富贵淫佚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则是宗室人口的膨胀,宗室成员的禄粮也就成为的一大财政负担。可见,明代中后期的宗室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经济问题。宗室成员无所事事,势必使宗室成员趋于分化:一方面,宗室成员进无门路,且又有丰厚的禄粮供给,于是就成为了一个“弃物”,对于与社会毫无用处;另一方面,一部分生活没有着落的宗室成员,开始游荡于社会,并与流氓无赖为伍。
在传统中国社会,因为倡导“人治”,缺少必要的“法治”精神,司法缺乏公正性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除非出现了包拯这样不畏强权的清廉之臣,否则在面对特权阶层的犯罪行为时,很难做到“违法必究”,甚至难免会出现徇私枉法之举。包拯因清明公正,而被民间百姓誉为“包公”,甚至将他的事迹编入戏曲、小说而广为传播,但从整个官场来看,真正能为百姓利益考虑且不畏强权的官员,确实寥若晨星,更多的还是和光同尘,甚至与地方豪恶、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同流合污。
《大明劫》剧照。
流氓意识与民间文艺
新京报:你在《无籍之徒》中谈到,流氓意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游民劣根性的烙印,具体表现为山头主义、土匪意识、见利忘义与雇佣意识。
此前,王学泰先生曾反复强调,戏剧、说书人、皮影戏等民间的通俗文艺,对于底层民众的价值观有着重大影响。有学者研究,义和团请的“神”,有很多就是来自戏剧。如你在《大明风华》所说,明代是一个世俗化的朝代,那么,这种民间的通俗文艺,对于流氓的意识层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宝良:关于这一问题,我在拙著出版的后记中,已经有一个基本观点的阐述,不妨在此再做一些申述。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流氓仍属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阶层,只不过是平民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而已,因此他们也有自己的意识与文化兴趣。尽然流氓是平民中的不良分子,即他们时常违法犯禁,与朝廷维系传统统治秩序的教化伦理凿枘不合,但他们的文化兴趣倒是与一般平民归趋一致。
这就是说,他们与渗透于平民阶层的俗文化相亲,而与士大夫的雅文化较为疏远。当然,不排除有些流氓头子,一旦成为暴发户以后,附庸风雅,藉此进入上流社会。一般说来,流氓识字不多,有些甚至大字不识几个,所以,其文化旨趣必然受到大众文化心理的影响。他们对朝廷确立的以儒家伦理规范百姓的做法极为反感,不愿做一个以耕织为生的“顺民”,而是希望摆脱土地的羁绊,到处游逛,自由自在。基于此,他们沾染了不少市民阶层中的不良习气,酗酒、、嫖娼样样来,而且在处事上不乏油滑、刁钻,有时甚至带有几分狡黠、诡谲,更有泼皮的胆气。在这些方面,他们与传统农民那种老实、胆小怕事、安分守己大相径庭。鲁迅笔下的阿Q与闰土,即是流氓与农民的两种典范。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统的农民意识在流氓中显然根深蒂固。尽管他们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但终究无法脱离农民意识的拘束。这显然是传统中国市民意识不独立乃至不彻底所致,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流氓意识的独立性。流氓与传统的农民在文化兴趣上有诸多的雷同之处:他们虽不愿对朝廷规范的官方祭祀活动表示尊敬,却与农民一样,对民间的宗教祭祀活动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有时甚至成为民间“社会”“庙会”的具体张罗者与者,佛道信仰以及民间的宗教信仰在这些人中仍然十分流行;他们对儒家经典虽无多少好感,对孔孟或儒家的先贤不屑一顾,却对流传于民间戏曲、小说乃至民歌兴味盎然,对梁山泊众绿林好汉肃然起敬,对关云长这样的忠义英雄更是顶礼膜拜。如明代苏州的流氓也是极喜山歌的,诸如《山坡羊》《挂枝儿》这一类的情歌,他们也时常挂在嘴边哼哼。
流氓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属于游民,因此其流氓意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游民劣根性的烙印,具体表现为山头主义、土匪意识、见利忘义与雇佣意识。流氓的结帮拉派,互相火并,形同水火,动辄斗殴,藉此抢夺地盘,山头主义的陋习根深蒂固。以历代农民起义为例,这种山头主义的坏习惯,必然会严重破坏起义队伍的纪律与内部团结,进而便于统治者分化与镇压农民起义。在流氓中,土匪意识也极其严重,烧、杀、抢、掠似乎成为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历代农民军为了维持生存而采取的“打粮”这一措施,实则是一种下山抢粮的行为。至于在明末广为流传的“贼过如梳”的谣谚,这决可简单地视之为污蔑不实之词,而是起义队伍中因流氓增加而造成的土匪意识膨胀的实录。
电影《新龙门客栈》剧照。
流氓虽以“义”字当头,以此联络同党,维系,但是,见利忘义之事也不断发生。流氓间各派互相拉拢,于是出现了一些流氓纷纷跳槽、各攀高枝的现象。而每当起义队伍处于最为艰难的时刻,队伍中的流氓就会动摇意志,经受不住朝廷的劝诱,投靠,最终出卖起义。在流氓中,雇佣意识也极其严重。为此,他们可以抛弃义气,谁有钱就替谁出力。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流氓就不仅仅是违法犯禁,成为朝廷的对立面,而是可以投靠豪强,成为打手、保镖,有时甚至成为朝廷的鹰犬,为统治者出力卖命。
戏曲、小说、词话、影戏一类的民间文艺,确实与流氓结缘很深。一方面,在传统中国,诸如戏子、说书艺人、皮影戏一类的江湖艺人,这些到处走码头的三教九流之人,无不被归入游民的行列。另一方面,自唐宋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戏曲、小说尤其繁盛,随之而来者,则是在儒、佛、道三教之外,新出现了一教,这就是“小说教”。当然,所谓的小说教,不过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而已,实则应该包括戏曲、小说、民歌、说书、弹词等民间文艺。所有这些民间文艺,均受到了包括流氓在内的城乡庶民的喜爱,并逐渐渗透到下层民众的意识中。
举例来说,很多流氓所取的绰号,如“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类,显然受到了小说《水浒传》的影响。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钱大昕曾明确指出,自从很多小说作品出来后,逐渐影响到民间百姓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也即“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所谓的“以杀人为好汉”,其实是指《水浒传》一书而言;而“以渔色为风流”,则指《西厢记》《金瓶梅》两书。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作者:陈宝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月。
乡绅与底层社会
新京报:我在读《晚清官场现象:杜凤治日记研究》一书时发现,地方绅士成为豪强,横行乡里,窝盗、窝赌,借重权势欺压平民的现象相当普遍。而《无籍之徒》541-554页显示,绅士勾结流氓无赖,在乡镇欺压普通平民。因为县官收税需要倚重绅士,因此也对绅士的某些行为视若无睹。
此前,有一些学者将古代宗法社会下的乡村描述为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但这些记录都显示,哪怕是同宗同族的熟人社会,其内部也存在着处于利益计算下的压榨和非法行为。也就是说,底层平民既遭受着皇权的压迫,同时也遭受着乡绅流氓的欺凌和剥削。纵然一些乡绅会做一些好事,但这一面也不可忽视。你怎么看?
陈宝良:这个牵涉到传统中国社会的认知问题。细说起来,又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二是传统中国地方社会中的社会力量问题。
就个问题来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社会性质有一个基本的界定,也就是将中国传统社会断定为一个“乡土社会”。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就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一个负责地方官员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于是,在乡土社会里,打官司也成为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在乡村里碰到矛盾,最为看重的是调解。而所谓的调解,其实又是一种教育过程。毫无疑问,将传统中国社会定义为以“无讼”为主体的“反诉讼”社会,大抵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但值得指出的是,历史研究固然需要这种概括社会本质的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但更应关注历史上社会形态的动态变迁,以及变迁的内在理路,进而阐释其原因。鉴于此,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与我都认为,到了明清时期,已经从“乡土社会”转而变为“好讼”社会。在明清史料中,“好讼”“喜讼”“健讼”“嚣讼”“刁讼”等,已经成为一些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更有甚者,至清代,时人已经将“积年健讼者”称为“讼油子”,而且此类健讼之人的广泛存在,已经称为滋生擅长“刀笔”之讼师的温床。“好讼”的各种面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告官之风的形成;二是家族内诉讼案件趋于频繁;三是土地诉讼案件的渐趋增加;四是妇女出面告状风气的形成;五是僧道涉讼案件的增加;六是地域性“好讼”之地的形成。由此可见,尽管儒家知识分子追求一种“无讼”的理想境界,而明清社会的现实状况却是一个“好讼”的世界。
《明代妇女生活》,作者: 陈宝良,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3年6月。
新京报:和平民相比,乡绅在地方属于强势者。
陈宝良:按照张研教授的研究,传统中国基层呈现出纵横依赖与相互联系的实际状态。而基层社会的构成,则包括以下三大系列:一是里社、保甲、坊厢系列,此属于法定社区中官方下令编组、反映了县以下基层行政的社会;二是家族、宗族、乡族系列,此为自然社区中人们长期以来在“物”和“人”的生产中自然形成,并以血缘、地缘为基本纽带的社会实体;三是行业与经济型乡族系列。
其实,上述三类社会,归根结底是绅士(亦可称“乡绅”,或称“绅衿”)在从中起关键作用。乡村基层行政,尽管绅士自己不曾出任担当,而是多由家无产业的无赖棍徒充任,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由社区自行推荐的特点,无疑使绅士可以借助自己的势力而操纵推荐,从而达到左右乡村社会的目的。而乡村宗族势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就是绅士势力的真实反映,一般庶民百姓不过是宗族的依附者而已。至于行业性的经济或同乡,当然无法否认商人在从中起作用,但绅商或绅董的出现,事实上已经证明绅士的势力同样已渗透到经济。所以,我认为,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其权力实际上操纵在绅耆(绅士与耆老)、乡保(里甲与保甲)与无赖层的手里。绅士无疑是地方社会的者,但无赖层势力的扩大,也造成他们可以更多地参与地方性社会事务。换句话说,传统中国的地方社会,不是绅士层独自在扮演者的角色,而是绅士层与无赖层互相妥协、互相渗透,共同管理或控制地方社会。
对于绅士与宗族的历史,历史学界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矫枉过正”的偏弊。就绅士这个社会阶层来说,在阶级史学的大纛下,难免过分强调了绅士的阶级属性,将其归类为贵族地主、特权地主之列,过分强调了这一社会阶层与统治者利益的一致性,也就是官僚、地主、绅士的三位一体。而西方学者的研究,则偏重于就科举、绅士作社会的研究,过分强调科举的“公平”性,以及绅士与土地的分离。其实,绅士除了是统治阶级的中坚以外,又何尝不与力量有冲突的一面,而且更多的是扮演朝廷与地方之间的一股中间势力的角色。
反观之,即使纯粹做一些社会学研究,也无法忽视对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的研究。这就是说,传统中国所特具的专制政府,必然隐含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显然的区别。每一个阶级都因那纵非对立也必然相异的利益,而与其他阶级截然有别。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至于绅士形象,同样必须加以辩证分析。正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所言,绅士阶层在乡里的活动以及他们的形象,实则存在着“恶”与“善”的两面:一方面,他们是“乡宦”,以乡里为根据地,在乡里厚殖资产,动辄利用自己在中央政府的地位与权力,横暴乡里,甚至招致“民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市隐”,拥有一定的科名及官位,因为对仕途绝望而居于乡里,虽较一般民众有特权的地位,但热爱乡里,与民众同甘苦。
就宗族力量来说,在阶级史学的旗帜下,族权被视为一根“绳索”,是套在家族内普通成员头上的一根绳索。所强调的是族长、族正等族内者(或者是地主)对族内普通成员(或者是农民或佃户)的盘剥,进而将族内成员形塑为一种紧张的阶级对立关系。这当然存在着偏差。当社会史广泛兴起之后,观察的焦点发生了转向,开始过分强调宗族在控制或稳定地方社会方面的正面价值,甚至将宗族内的生活形塑成一种温情脉脉的理想状态。
其实,这同样具有片面性。若是认真梳理明清家族史,因“好讼”之风的兴起,家族内同样存在着诸多的争竞,甚至分家成风。在明代,号称天下有“三大家”:个是凤阳的朱家,具有皇族的身份;第二个是曲阜的孔家,世袭衍圣公;第三个是龙虎山的张家,在元代被封为“天师”,至明代被降格为“真人”,也是世袭的。即使是名头如此之大的三大家族,如果我们去仔细阅读一下《明实录》,不难发现如下事实,即三大家族内,不但无赖的丑行比比皆是,而且在家族内部,同样为了利益而尔虞我诈,甚至不乏斗个死去活来。
历史的真实往往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历史研究的兴味与价值所在,恰恰也在于揭示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最为重要的一点,理应具有一种辩证的思维,而不是将历史问题简单化甚或片面化。
采写/释枷
编辑/李永博 王铭博
校对/赵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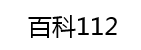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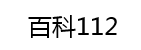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蜀渝麻将怎么开挂”(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蜀渝麻将怎么开挂”(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