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
回想娘的一生,爱干净、很要强,自力更生不求人、体虚志坚最刚毅。爹去世的早,她拉扯四个孩子非常不容易,但是她很少求人,总是自己独立承担。娘快人快语,思路清晰,办事情从不优柔寡断。娘喜欢干净,身上常带着手帕,手脸清清爽爽,吃饭细嚼慢咽,吃完总是很仔细地擦擦嘴、擦擦手,弹掉不小心掉在衣服上的饭粒。她的头发很齐整,梳理得利利落落,所以看起来总是精神抖擞。
爹走那年,娘五十来岁。作为她最小的女儿,我也已经结婚,而且有了三个儿子。娘的另两个女儿,一个嫁到了一路之隔却分属两个不同省份的村庄,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另一个嫁在了本村,也有了三个儿子。娘不光有这么多外甥和外甥女,唯一的一个儿子也有了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所以,她应“姥娘”的时候,会笑盈盈地说,我有一大帮“龟孙秧子”,这几个是老宋家的,那几个是老褚家的,还有那仨小点的是张楼的。
有时候,我也很奇怪,她很少对人家讲我是老张家。大姐二姐,在她那里都是老宋老褚张口就来;到了我这,却变得隐晦。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孩子,在她心里我永远都是那个灾荒年代拖家带口去东北讨饭时被她紧紧抱在怀里的“小妮子”,即便我嫁了人有了自己的孩子,在她的眼中我依然是她的“小闺女”。
姊妹三个离得不远,相互走动也便多了。其实,说是相互走动,倒不如说是一起相邀、隔三差五回娘家。二姐在本村自不必说,大姐虽然“远”在江苏,实则离娘家也就四五里地。大姐回娘家,必定路过我的家。因为那时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她便常常“不期而至”推开了我的家门,“上咱娘家去吧!”
那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推着一辆大梁自行车,车前杠上坐着老二老三,车后座上坐着老大;大姐蹬着三轮车,车厢里是我的大外甥和小外甥女,而大外甥女已经懂事了,会跟在车后面,帮着推推车子。所有的孩子都叽叽喳喳有说有笑,把我和大姐的“唠叨”声淹没,大人小孩一路浩浩荡荡乐呵呵地向“姥娘”家的方向出发!
不远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那时候,物资不像现在这般丰富,什么鸡呀鱼呀肉呀的想买就买。我们姊妹三个不会空手,但也只是带去一些最普通的“吃食”,比如院子里自己种的青菜、集市上买的刚打上来的鲤鱼、代销店里买的新出的点心、路边摊上买的应季水果。每次,大姐二姐总是会买很多东西;她俩还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我买,到家却跟娘说,“你看看小三,不让她买这买那,她偏不听”。娘笑笑,再数落我一顿。
大嫂是个热心肠,脸上总是笑嘻嘻,腿脚也勤快,忙活这忙活那。她让我们姊妹仨陪着娘说话,让孩子们一起出去玩,自己却“马不停蹄”地拾掇起中午的饭菜。厨房好像欢快的“拖拉机”,灶台里冒着白色的水蒸气,伴着炉膛里的烟火气,不大会儿就香气四溢。
娘哪是一个能闲得住的人。她最多和我们聊上一会,便去厨房察看,帮着儿媳妇炒菜、蒸馒头、焖米饭;然后,匆忙来到大街上,找寻她的一众“龟孙秧子”,捎带加上自己的五个孙子孙女。看到大孩子小孩子们能玩在一起,她放心了许多;却也会被不时传来的哭闹声打断,抓紧去安抚。她会一把抱起哭闹的外甥,“呵斥”挑起事端的孙子;她会假装要伸手打调皮捣蛋的外甥,却把巴掌轻轻落在了一脸无辜孙子的屁股上。她总是这样说,闺女家的孩子那可都是“人家”家的宝贝,人家爷爷奶奶都不知道疼多厉害呢,可千万不能在姥娘家受了委屈。
我常想,娘这种“和稀泥”甚至于“拉偏架”的方式有些欠妥。曾经问过娘,这样对大哥家的孩子太苛刻;娘却说,小孩子们打打闹闹、磕磕碰碰,都是无心的,哪有什么谁对谁错?都是自家人,非得要断出个你有理他有错,那还叫一家人吗?
最热闹的时刻莫过于吃饭。娘本想安排两个孙子和外甥女们一桌,三个孙女和外甥们一桌,奈何外甥太多,外甥女只有两个,便做了罢,最后变成大孩子们一桌、小孩子们一桌。娘一边和我们拉家常,一边竖起耳朵听孩子们的动静,一旦有“杂音”出现,便撂下碗筷前去制止:虽不是一样的情景,却是一样的处理方式,情愿护着外甥外甥女,哪怕孙子孙女根本就没吱声。
“你看看俺娘,哪有你这样惯孩子的!再说了,你孙女人家都没说话,是你外甥找的事,你咋不凶你外甥?!”大姐二姐,包括我,总是不约而同地向娘“开炮”。
“没事,没事,咱娘咋说就咋办!”大哥总是很虔诚地说,我看得出来大嫂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不“心甘情愿”却也无可奈何。
“你这样疼外甥,恁外甥长大了还不一定疼你呢?你没听说,外甥是姥娘家的狗,吃完喝完还拿着走?”有时候,我会调侃一下。
娘总是笑笑,“辩解”着,大概意思就是俺不指望着外甥外甥女们以后孝敬俺,只要他们好好上学有出息,长大了以后知道孝敬父母孝敬爷爷奶奶就行了。
就这样,一晃过去了好多年。我的孩子都上了大学,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大儿子在微山,二儿子在上海,三儿子在南京,我开始了天南地北“溜乡”看孙子的漫漫征程。五十来岁的我,身上有了各种毛病,血糖高血压高,腿还经常疼。在儿子“钢筋水泥”般的楼房住时间长了,我更加想念老家,尤其是想念自己的老娘。无数个夜晚,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娘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娘的话语也在耳边一遍遍响起,“妮儿来,在外面给孩子帮忙照顾孙子孙女,这是你当奶奶应该的;娘没啥事,能吃能喝,还能拄着拐杖四处溜达溜达,你不要挂念娘,照顾好自己就行。”
终于“熬到”回老家的日子!我心急火燎地跑去看娘,娘每次都在那个熟悉的路口,张望着我回家的方向。近了,越来越近了,我看到娘的背驼得更加厉害,身高也缩短了不少;唯一没有变的,是看到我来到眼前脸上马上出现的笑容。我搀扶着娘,一起慢慢往家走。在路上,娘一遍遍说起从前的事,原本听着很烦、觉得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我,此时此刻听起娘的话语,格外亲切。
“还记得不,娘,开新他们小时候在家里怎么调皮捣蛋,你都不打不骂,这是为什么呢?”
“憨妮子哟,娘不是觉得孩子们在姥娘家不受气,你在婆家更好相处吗?!”
我愣住了,心中五味杂陈久久不能平静,最终被一股浓浓的暖流包围。
时间证明了,“外甥是姥娘家的狗,吃完喝完还拿着走”,这话不完全正确。我的孩子,还有大姐二姐家的孩子,从小在姥娘家有吃有喝有玩有闹,却没有成为喂不饱没良心的“狗”。相反,所有的孩子们都十分孝顺,不仅仅孝顺自己家的爷爷奶奶,也非常非常孝顺自己的姥娘。大哥家的孩子,我的侄子和侄女,都非常懂事,跟姑姑们、老表们知冷知热。孩子们知道姥娘喜欢喝鸡蛋白汤,喜欢喝老年奶粉,不吃牛肉猪肉鸡肉、只偶尔吃些鱼肉和羊肉,过年过节回家的时候,都挑选最好的买给姥娘。
突然明白了,娘的“和稀泥”式教育,不是瞎搅和、也不是趟浑水,而是一种大大的包容和博爱,让孩子们懂得家人之间要礼让谦和;这样一来,以后走向社会,待人接物也能把握得恰如其分。
娘的生日是农历五月五——端午节。对于我家来说,这一天是盛大的集会。外甥外甥女们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带着对象和孩子,一大家子人济济一堂,祝福姥娘生日快乐、长命百岁。我曾开玩笑地问娘,“他们小时候闹别扭,你都是一把抱起这个、一把又抱起那个,现在试试还能抱得动不?”
娘愣了一下,或许也是年纪大了耳朵有些背,又或者是被我突如其来的刁钻发问弄得措手不及。我又问了一遍,娘这回听得真切,依旧笑嘻嘻地说,“憨妮子哟,你看看俺这些外甥,一个个都长成大小伙子了,别说是他们,就是他们的小孩子,娘都抱不动了!”
儿子偷偷告诉我,他想给姥娘一百块钱,又怕姥娘不会收,便放在了她的床褥下面。我抽时间告诉了娘,娘执意不要,说自己花不着钱,而且孩子们正是用钱的时候,可不能乱花钱。“一百块钱,可不少,你们都给我买这买那,娘还上哪去花也?!”
一番争执不下,娘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她把钱给了我,说是就当自己已经收下了外甥的孝心;然后把钱给了闺女,这是当娘的一片心意。“我都多大了,咋能要你的钱?”
娘的回答,我至今难忘,“妮儿呀,你再大也是娘的娃。”
年,娘的身体每况愈下。好在,那年的端午节,娘挺了过来。只是,她变得越来越糊涂,有时候不认人了。她记不起自己中午吃的什么,也记不清自己外甥的名字,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是,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孩子。我的侄子会半开玩笑问她,你知道俺三姑是恁啥吗?她喊你啥?娘虽然有些迟疑,却也能准确说出我是她的闺女、我叫她娘……
娘最后的时光,是躺在床上度过的。那时候,已经进入了阴历七月,天气炎热。娘躺在老家堂屋西侧的床上,她的身上盖了一层薄薄的毛毯,却也遮掩不住那皮包骨头的身躯。用什么去形容呢?儿子告诉我,俺姥娘现在瘦骨嶙峋、骨瘦如柴,就像报纸一样单薄。我靠近她,试图和她聊聊天。她的手伸向我,嘴里已经说不出话;但我知道,她肯定记得我,那是她牵肠挂肚的小闺女。
还是曾经那双无比有力的手臂吗?那抱着我去东北讨饭时,坚强有力的手臂;那抱着我的孩子,想方设法哄外甥的温暖手臂;那虽然已无力,却能够拄着拐杖四处张望搜寻女儿归来时身影的手臂……都去了哪里?
娘走的那天,正好是七夕。我就想,娘的命挺好的,生于端午、殁于七夕。每当吃起粽子时,我想不到什么屈原投江自尽,却能想到那是娘出生的日子;每当坐在葡萄架下,我看不到什么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却能想到那天娘去了天上和爹团聚……
壹点号 新哥来了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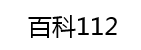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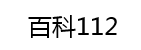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吉祥四川麻将挂多少钱”(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吉祥四川麻将挂多少钱”(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