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桐柏、泌阳两县交界处,有一座海拔459米的盘古山,传说为当年创世神盘古开天辟地、造化万物之处。为了纪念这位传说中的创世始祖,人们在其高峰处修建了盘古庙,庙内塑有盘古像。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这里还会举行盛大的盘古庙会,数万人从各地赶来祭拜盘古,逐渐发展为集文化旅游与经济开发于一体的盘古文化节。2005年12月4日,经中国文联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实地考察论证,泌阳县被正式命名为“中国盘古圣地”。2008年6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桐柏、泌阳两县联合申报的盘古神话被列入第二批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伴随各种资源整理活动,与盘古相关的各类神话传说得到搜集研究,盘古同女娲、夸父等神话形象一道,共同成为中国神话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见于《山海经》《周易》《楚辞》等秦汉典籍的神话形象,盘古出现在文献中的时间要晚至三国时期,相关问题聚讼难已,可谓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独具特色的典型形象。回溯分析盘古形象的流变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创世神话的具体表征,并据此体会盘古在其中显现的文化符号价值。
本土或西来
1904年,日本学者高木敏雄在《比较神话学》一书中指出,印度《摩奴法论》中记载有梵天金蛋创世神话、《梨俱吠陀》中记载有原人布尔夏尸化宇宙万物神话,这与文献典籍中记载的盘古创世神话具有相似性,通过比较可知,盘古创世神话来源于印度文化,是随着印度佛经传入中国后产生的。
这种外来说在很长时间内对相关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认同者有之,并通过更为深入的具体研究为外来说提供了更多文献证据,如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1939年便撰写《盘古考》一文,列举《外道小乘涅槃论》《摩登伽经》中的尸体化生神话为证,论述盘古形象当受印度影响而产生;反对者亦有之,也尝试从不同角度证明盘古神话出自中国本土,其中既有茅盾、袁珂等知名学者求索民间,依据南方少数民族中留存的祭祀仪式认定此当为盘古形象源头,也有以马卉欣为代表的学者上溯文献,以《路史·前纪》引《六韬·大明》云“盘古之宗不可动也”为据,认为“盘古”在先秦典籍中早已见录,种种讨论不一而足。
推究上述诸家论点,无论外来说还是本土说均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且相关论证亦可见逻辑倒置、由果推因之处。重新回顾有关盘古的文献记载,可知引发来源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盘古迥异于其他神话形象的成形时间。因此,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有二:其一在于为何秦汉文本中不见有关盘古的记载;其二在于为何在三国时期吴国人徐整的著述中又出现了盘古这个神话形象。
想要回到秦汉时期的神话语境当中,理解当时创世神话的具体表现,最好的切入点非《山海经》莫属。《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至汉代初期,以地理志的形式记录了远古时期人们想象出奇的思想活动。在其光怪陆离、充满奇幻想象的文本中,保留了数则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创世神话: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启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长千里,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依据方韬的注解,“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中的“献”为托举之义;而“印”则通“抑”,为向下按之义。由此可知,在这段记载中,重和黎兄弟二人的工作在于通过动作“区分”天地,而并非凭空“创造”天地。这也就提示了一个关键信息:在此类创世描述中存在某些先决条件,例如“天地”这类原始世界中的自然实体,便默认是早于重和黎到来就已经出现的客观存在。再如《山海经》中有关“烛阴”与“烛龙”的两段神话传说,根据文本记载,烛阴睁开眼就是白天,闭上眼就是黑夜,吹气就是寒冬,呼气便为炎夏,颇为类似于西方创世神话类型中的化生型神话,但在这则神话传说中烛阴代表的却并非“世界”本身,而仅是钟山之神,也就是世界的组成部分,烛阴之外更为广阔的天地范围显然也是默认存在的。同理,能请来风雨的烛龙依据《山海经》的描述也更像是创世神话的参与者,而并非这个世界的原始创造者。
(明)胡文焕编《山海经图》中的烛阴像
这正是中国古代创世神话的最显著特征,不论是《山海经》中这些散碎记载,还是我们更为熟悉的女娲造人神话等,以创世神话语境来看,它们都并非揭示世界从何而来的原始创造,而更像是在特定基础上发展完善的次级补充。由此可知,相较于探索世界的源头出处,华夏民族的先民们更加关注有关于“人”的神话母题。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发生在远古时期的重大事件“绝地天通”具有密切关联。
依据《国语》记载,所谓“绝地天通”,本质上是一场对原始神权的厘清与限制: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根据文中描述不难看出,“绝地天通”发生的背景在于“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意即随着少皞氏的衰落,原有祭祀秩序被打乱,人人都可以自己举行祭祀仪式与上天沟通,原本神权的权威性遭到严重破坏。为应对这种情况,颛顼采取的行动是命令重和黎分别廓清天上的众神与人间的民众,让两者相互隔离,不再能够直接沟通。由此回看《山海经》中“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的描述,则极有可能正是对这一神权清理过程的直接反映。
从结果来看,“绝地天通”极大程度上压缩了神权的拓展发挥空间,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自此断绝了与上天或神祇的直接联系,只能更加专注于现实的人间生活。这不仅避免了古代中国走向神道设教的神权社会,同时在农耕传统的联合作用下,也进一步影响了华夏民族逐渐形成关注现实、强调实用的日常生活观念。
从神话传说发展演变的历程来看,“绝地天通”事件有着重大影响。正如茅盾在《神话研究》中所言:“开辟神话就是解释天地何自而成,人类及万物何自而生的神话。不论是已经进于文明的民族或尚在野蛮时代的民族,都一样有他们的开辟神话。他们的根本出发点是相同的——同为原始信仰,但是他们所创造的故事却不能尽同。”传世神话的核心依据在于本民族的原始信仰,“绝地天通”的发生使华夏民族的原始信仰演进速度大大提升,迅速结束了带有蒙昧与奇幻色彩的想象时代,并在思考与总结的作用下进入了理性时代。相较于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人们更愿意相信现实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视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并逐渐发展出完备的史官制度为现实生活提供指导。从这个角度来看,秦汉文献中少有对创世神话的总结整理,因此并未出现盘古的形象事迹也就不难理解了。
“道”的显化
学界公认最早记载盘古形象的文献典籍,当属三国时期吴国人徐整所著的《三五历记》一书。该书在元代前便已亡佚,今日所见为《艺文类聚》中的残本: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首先值得注意的便是开头“天地浑沌如鸡子”一句,自高木敏雄起,无数学者在研究盘古神话时习惯据此将其视作西方神话母题中的“宇宙卵”类型加以思考,但结合中国古代天文思想观念的发展历程来看,“天地浑沌如鸡子”实际反映的是盛行于汉末三国时期的“浑天说”。
出于农耕文明的实际需求,中国古代发展出一整套发达完备的天文历法知识。而在宇宙结构认知方面,古人则先后经历了“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几个阶段。在殷末周初时期,人们信奉“盖天说”,即著名的“天圆地方”观念,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穹隆状的天空覆盖在方正平直的大地之上,周边则有八根柱子作为支撑。依据古代神话内容不难看出,共工怒触不周山与女娲炼石补天等早期著名神话传说显然均产生于此种认识背景之下。
而伴随认知水平的提升,先民逐渐意识到“盖天说”的不合理之处,以张衡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浑天说”,并逐渐在东汉时压过“盖天说”占据主导地位。关于“浑天说”最具代表性的描述,当属《晋书·天文志》中葛洪所引《浑天仪注》的内容,指出天并非半球形的盖状,而是一个类似鸡蛋般的完整圆球,地则如鸡蛋内部的蛋黄那样居于其中,两者如同车轮般不停转动:
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
将《浑天仪注》的内容与徐整《三五历记》的记载相对照,可见盘古诞生时“天地浑沌如鸡子”的描述正符合时人的宇宙认识观念,若强行将其解读为“宇宙卵”类型的神话母题,则未免有南辕北辙之嫌。
真正能揭示神话核心的内容,当属“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这句。乍看之下,这个说法似乎与前文论及的“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颇为类似。但实际上其中明确指出了“天”与“地”不同的物质构成:代表“阳”的清气上升构成天,代表“阴”的浊气下降构成地,“阴阳”“清浊”等对立概念很容易让人由此联想到道家学说中的基本观点。
细数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观点,道家以探讨宇宙本源、强调哲学思辨而著称,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个从哲学层面系统论述了宇宙起源问题。《老子》四十二章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田子方》中进一步阐发老子的阴阳观点为:“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其中蕴含了阳气生天,阴气生地,阴阳二气交通而万物生的宇宙生成模式,而这正是《三五历记》中描绘盘古所处混沌环境的理念来源,由此可见盘古创世神话的出现与道家思想观念存在密切联系。
两者间具体存在怎样的联系呢?这与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环境与道家发展新变息息相关。东汉时期是思想领域的道家思想演变转化为宗教领域的道教团体的关键确定期,至东汉后期黄老道学逐渐形成实体,太平道、天师道等民间原始教团相继成立,加之此期战乱频发、社会动荡、疫病横行等社会现实因素,能够治病弭灾、修身养性的道教获得长足发展,以《太平经》与《老子想尔注》为代表的教派教义文献也随之出现。此类文献为方便信众接受,往往脱离原初的道学思想表达而更强调宗教实用意义。如《太平经》以阴阳五行学说勾勒理想社会图景,提出财产共有、自食其力的善恶报应观念;《老子想尔注》则往往通过增删、改字等方法修改《老子》原文,使之更加符合本派教义。
结合上述材料不难看出,宏观上讲,从道家思想演化为道教流派的过程,就是一个由虚转实的过程,是将虚无缥缈的哲学思辨转化为能被信众接受的价值观念。而道家思想中关于宇宙本源的思考辨析显然是相对难以转化的部分,如何将道家思想中难以描摹的核心概念“道”显化为某种具象化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看,构建一个符合道家思想观念的创世神话故事显然是颇为有效的转换手段。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三国时期在吴主孙权的倡导下,道教在吴国发展迅猛,孙权本人更是笃信道教,雅好神仙。吕蒙病危之时,孙权曾派遣道士为其请命;虞翻出言不逊贬斥神仙,孙权便将他贬谪到偏远的交州。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道教在吴国广泛传播,一时间蔚为大观。
基于这样的社会基础,为何吴国人徐整能够在著作中创造出符合道家宇宙本源认识的盘古创世神话形象,或许也就不难理解了。显然在这则后出神话中,盘古的形象可以被视作道家思想中“道”的具象化显现,故而据此将盘古形象视作“中国古代本体思想的具体表达”,可谓切中问题肯綮。
斧自何处来
回顾早期文献记载中的盘古形象,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起初盘古手中是没有斧子的。这件在现今盘古神话故事中颇为重要的道具并非伴随盘古形象诞生,而是在经历漫长发展演化过程后,最终加入盘古创世的神话故事。
那么,问题随之产生:盘古用来开天辟地的斧子究竟来自何处?前辈学者论及此问题时,大多认为最早记叙盘古持斧的文献材料当为明代周游所著演义小说《开辟衍绎》。
《开辟衍绎》,又称《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全名为《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共六卷八十回,讲述了自盘古开天至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其首回回目便为“盘古氏开天辟地”,但内容除了我们所熟悉的盘古创世神话外,还明显融合了其他文化中的元素:
昆多崩姿那受佛命毕,只得顶礼辞别世尊并诸大菩萨,驾一朵祥云,离了西方佛境,直来至南赡部洲大洪荒处,大吼一声,投下地中,化成一物,团圆如一蟠桃样,内有核如孩形,于天地中滚来滚去;约有七七四十九转,渐渐长成一人,身长三丈六尺,头角狰狞,神眉怒目,獠牙巨口,遍体皆毛;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此而混茫开矣,即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变化,而庶类繁矣,相传首出御世。从此,昆多崩娑那立一石碑,长三丈,阔九尺,自镌二十字于其上曰:
吾乃盘古氏,开天辟地基。
亥子重交媾,依旧似今时。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开辟衍绎》文本内容乃是周游依据余象斗所著演义小说《列国前编十二朝传》抄撮而成。比勘两书内容可以发现,除了书名、目录、插图、序跋不同外,两书正文内容只有细微差异,而刊刻于崇祯二年(1629)前的《列国前编十二朝传》显然成书要早于崇祯八年(1635)刻印的《开辟衍绎》。对比两载盘古创世的内容亦可证明两书间沿袭有序,故而可知持斧盘古的形象最早当见于《列国前编十二朝传》。
两本上古史演义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当属其在道教创世神话的基础上增加了佛教的文化背景,塑造了与盘古融为一体的角色昆多崩姿那,并将盘古开天辟地解释为领受佛命,完全舍弃了原本神话故事中的道教内涵,变成一个彻底的佛教故事。这种拼接处理使佛道两教思想内容在演义故事中融为一体,显现出迥乎于原始神话传说故事的独特样貌。
而除了一目了然的佛道文化融合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显然是首次登场的盘古之斧。《三五历记》中作为“道”的化身的盘古形成于混沌虚无之中,自然也不需要任何道具实现天地开辟,否则本来就空无一物的虚空世界中又何来一柄利斧呢?但在明末的演义小说中,基于佛道融合的故事背景,作者安排昆多崩姿那持有由“神力”凝结的利斧看上去也同样合理。但为什么当作者认为盘古需要借助外力时,会选择斧子作为盘古的工具呢?
有学者指出这种选择或许来自先民观察闪电时产生的真实感受。在自然界中霹雳闪电往往能够造成瞬间劈开乌云、划开天宇的视觉效果,在古人眼中便仿佛如同给天空劈开裂口,因此作为自然现象的霹雳闪电,经常被设想为威力巨大的天神武器。而当神话创作者需要设计一种能够开天辟地的武器时,便往往会选择利斧之类用于劈砍的锐器,并时常会为其增加雷电属性。
具有类似特征的神话传说在其他民族中比比皆是:在位于西亚的古赫梯文明中,善于打雷的天神便手持巨斧;巴比伦与亚述人信奉的雷电之神阿达德(Adad)在壁画中的形象同样是左手执闪电、右手持斧子;我们熟悉的以雷霆为武器的希腊主神宙斯,也经常被表现为手持霹雳斧的形象。这些实例说明在古代神话角色使用的劈砍工具选择上,各民族间展现出了基于同类生活经验的共通性选择。
而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表现来看,将开辟之事与斧凿工具相联系的做法亦早已有之。南宋诗人范成大便曾经在面对无垠的晴空时,写下过“不知几斧凿,成此太虚空”(《午坐》)的诗句,虽然不能将诗篇中提及的“斧凿”断言为盘古所持之物,但当面对广袤的天地之时,诗人不自觉遐想天地间的划分乃是斧凿的产物,亦可从中看出这两样工具的选择的确合乎民众认知,就实现开天辟地而言可谓是最为合乎情理的选择。
从“补完”到“开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学者始终认为中国古代缺乏系统的神话传说谱系,特别是在创世神话领域更是付之阙如。为打破这种偏见,许多中国学者苦心孤诣,通过各自的研究证明中国古代不仅有创世神话,而且内容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属叶舒宪,他依托《新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创世神话的类型与理论”词条归纳出了五种创世神话类型,并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资料逐一进行原型重构,最终得出结论:人类古代创世神话的所有类型在中国古代典籍均能找到对应例证,由此说明中国古代拥有丰富的创世神话资源。
山东沂南北寨汉代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与盘古像
然而,结合前文论述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以盘古事迹为代表的创世神话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补完”,它建立在道家思想基础上,是从道家向道教转化过程中对“道”的一种具象化显现,因而具有迥乎于西方神话模型样态的独特特征。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此类神话形象时,不仅要参考西方理论学说,更要特别关注其中蕴含的本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特色,发掘其中更为深层的文化价值,在认清其“补完”意义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站在本民族文化高度,作出更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阐释与判断。
(本文注释已略去)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3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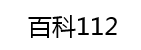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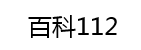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蜀渝麻将怎么开挂”(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蜀渝麻将怎么开挂”(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