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烟威文学》作者:权万仓
老村实在是太老了。我不知道她诞生于何时,只是听老人们说,我们的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岁月,大概只有渭北高原上那纵横交错的沟壑知道。
自打我记事起,老村就是一副破败不堪的模样。一排排土夯的院墙残缺不全,墙头上长满了乱蓬蓬的茅草;有的院墙早已倒塌,只留下一点点高低不平的地基。一些窑洞上面的挡土墙也垮了,顶部的砖头露在外面,被风雨剥蚀得参差不齐,如犬牙一样地向外呲着。坑坑洼洼的村道两旁,杂乱地分布着茅房、猪圈、粪堆,散发着令人厌恶而又熟悉亲切的味道。下雨的时候,雨水卷着人畜的粪尿,流入一口口十来米深的水窖,就成了人畜赖以生存的饮用水。
老村曾经有三棵参天古树,一棵槐树,两棵皂角树,树干都有两三抱粗,是鸟类栖息和人们夏季纳凉的好地方。特别是村子中央的那棵皂角树,树冠差不多有半亩地大。夏天,全村人坐在树下开会,一半的树荫就足够了。树干内部早已腐朽,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空洞,成了孩子们躲猫猫玩耍的乐园。
古树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像宝贝一样被保护起来,说不定还能吸引不少的游客。可是,在七十年代初的新农村建设中,都被连根挖掉了。我家门前也有一棵正当壮年的皂角树,一抱多、粗枝繁叶茂,每年结出的皂角,足够半个村的人洗衣使用,也未能幸免。
记忆中的老村,虽然衰老破败,却并不寂寞。那时候,村道南面的麦场边上立着一根高高的木杆,上面挂一块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破铁板。每天上工之时,队长拿一把铁锤,或捡一块石头敲打铁板,铛铛铛的声音传遍全村,社员们呼啦啦聚到一起,按照队长的安排,或下地劳动,或学习开会,好不热闹!村旁的小学校园里,不时传来朗朗的读书声,或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老人们也走出家门,夏天在树下乘凉,冬天在墙根晒太阳,三五成群地谈天说地。工余时间,村头便成了闲话中心,人们在这里谝闲、抬杠,上谈大事,下扯鸡毛蒜皮,虽然也免不了家长里短,弄出点是是非非,但总归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热闹红火的背后,是难以摆脱的贫穷。老村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越来越无力养活嗷嗷待哺的儿女。尽管人们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甚至喊着“大干快上”的口号挑灯夜战,打着“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标语苦战新年,但仍然免不了为吃饭穿衣发愁。大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老村持续地变老、变丑,却毫无办法。
1979年实行包产到户,老村没有了集体出工的火热排场,却似乎有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人们发疯似的往地里跑,深深地犁地,多多地施肥,一遍一遍地锄草,像侍弄自己的孩子一样地侍弄土地。汗水没有白流,当年种下的小麦,第二年夏天便获得大丰收。
到了收获时节,麦场上欢声不断,笑语连连。每天下午,不管谁家碾麦结束,无需任何人,全村人都会自带工具,到麦场帮忙起场、扬场、堆垛,一点都看不出分田到户的样子。主人反而插不上手,赶紧回家做菜做饭,准备招待帮忙的邻居们。打场完毕,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丰收,比过年都要热闹。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我都会为老村纯朴的民风而感动!
此后不久,我当兵去了遥远的新疆。这一走,就是40余年。但每次探亲回乡,都能够感受到老村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一座座新宅拔地而起,老村扩大了足有两倍。我的同代人及其后代,大都搬进了宽敞漂亮的新宅。老村似乎如凤凰涅槃,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重生!
我曾经幻想着,退休后效仿古人告老还乡,把荒废的祖宅收拾一番,住下来重续乡情,过一过田园生活。哪承想,等退休后再回老村,却又恍若隔世。偌大的村子,竟变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以前回乡探亲,从进村口到入家门,我都要给乡亲们发几包烟,这个打打招呼,那个说几句话,不足百米的路往往要走上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这次回村正值冬季,我依旧准备了几包烟,可穿过整个老村,连个人影都没看到。等我从地里给父母烧纸返回村子,终于见到一个人,是隔壁家婶子。我问她,村里人都去哪儿了?她告诉我,人都到县城去了,老村就剩下两个老婆,村东是我,村西是红红他妈。我当时脑子里冒出的个念头是:这两个老太太胆子真大!
后来才了解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随着进城打工、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以及推进城镇化的政策支持,农民在城里买房已成普遍现象,不少老村变成了老人村甚至是无人村。过去,每个村都有小学,有的大村还开办了中学。现在,全镇几十个村子,只有镇政府旁边的一所学校,从小学到初中,总共才200来个学生,其他都到县城上学去了。一些老人本不愿意离开村子,但冬季窑洞里没有暖气,也只好跟着孩子们进城过冬,老村就变成了真正的空巢村。
人进城了,但村里的地还得种呀!不过,现在种地,也与过去大不相同。年轻的村民们,不一定非得掌握种田技术,到了相应的季节,打一个预约电话,然后回村等待约好的耕地机、播种机、收割机来耕作就可以了。如果本村有农机经营户,对各家土地比较熟悉,电话里谈好价钱就行,连回村都省了。只有少量机械难以完成的农活,才回村忙活一阵。
村里多数人家都有小汽车,回村也非常方便。过去,我们去县城要翻越一条大沟,走一个半小时的路;现在,沟上架起了大桥,双向四车道的高等级公路直通村口,从县城回村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站在又一次走向衰落的老村村口,我忽然产生了一种穿越的幻觉。在这里,我们曾经用石碌碡碾麦、石碾子碾米、石磨子磨面,石臼石杵更是各家必备的生活用具;在这里,我们曾经住土窑洞、穿粗布衣,用牛拉犁、人撒种的方式耕种土地,睡过土坑、拉过风箱,还推过据说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独轮车;在这里,我们用上了电灯、电话、拖拉机、汽车,直至进入到今天的信息时代。我们似乎从石器时代走来,经历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座座古老的村庄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快速嬗变。有的除旧布新,浴火重生,变成了整洁漂亮的现代新村;有的则人去村空,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但谁又能说,这种不可逆转的衰落,不是另一种意义的重生呢?
渭北高原上的大多数老村,都有着严重贫瘠的先天缺陷。长期以来,人们这片几乎完全靠天吃饭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却总是过着缺衣少食的艰难日子。即使如今种地不再纳粮交税,甚至还能够享受一定的政府补贴,但仅靠种地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而已。
老村的儿女们,自古就有着深厚的故土情结。这种融入血脉的朴素情感,激励着一代代老村人,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而不懈奋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思维拘囿于这片小小的天地。温饱即知足的生活态度,长久地束缚着人们走向富裕的步伐。令人欣喜的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老村人,思想更加解放,梦想更加高远,他们要甩掉老村这个重重的壳,破茧成蝶,展翅高飞,去追求更加幸福的新生活。
也许有一天,老村会彻底消亡,变成现代化的农场,变成信息化的工业园区,变成一幢幢高楼大厦,变得连她的儿女们都再认识。但我相信,未来的老村和她的儿女们,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文中插图由陶玉和、田明山老战友拍摄,与所述老村无关——编者)
作者权万仓,陕西澄城县人,1963年1月出生,1981年10月入伍,从军37年,年3月退休。爱好文学、摄影,在军内外报刊发表新闻、文学、摄影作品数百篇(幅)
壹点号奎先达坂西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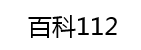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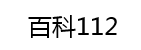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微信麻将开挂后特征”(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微信麻将开挂后特征”(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