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我们在这里主要讲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而非家庭和社区里的非正规教育,通常被视作传授在任何特定社会中被认为重要的知识与技能的途径。对教育的讨论往往建立在一系列观点上:孩子们该如何学习,什么方法教会他们的效率最高,还有教育帮助孩子习得了那些让他们在社会上能够立足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在获得学历、找到工作、拥有经济保障方面,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与广义上他们对孩子未来生活的期望是呈强相关的。当然,也并不是全世界的家长都能有机会选择孩子在何时何地接受教育;全球受教育机会的分布一直都反映出不均衡的态势。虽然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教育机会有限,但对全球的大多数家长来说,孩子的教育都是他们担忧的重点。
在一些地方,父母们担心的是孩子能不能得到哪怕一点点的教育,为此的投入会不会贵到他们支付不起(或者,就算上学能免费,孩子需要的书籍、校服和文具他们能不能买得起);而在另一些地方,人们关注的可能是孩子能上哪一类学校,以及学校对孩子的学习、社交和情绪发展,以及孩子未来的机遇和社会流动性的影响。
《为人父母:那些证据告诉我们的事》,[英]维多利亚·库珀 [英]希瑟·蒙哥马利 [英]基伦·希伊 著,白亦玄 译,企鹅兰登丨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版。
孩子想从学校里获得什么?
孩子才是学校和教育体系的核心:这一点显而易见,不证自明,但是直到近些年,孩子的想法才被考虑到,甚至才有人开始重视。教育经常被看作父母的选择,而不是孩子的选择,而这二者之间又有着巨大的差异。至少在理论上,孩子是越来越有权利做出影响自己一生的决定了。
尽管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已经建立起了这个理念,但是鲜有文章从儿童的角度来探究学校这个概念。采用了儿童的视角的研究表明,成人与儿童对同一环境的感知差异往往是悬殊的。虽然有些孩子可能会“用脚投票”,但孩子在择校问题面前依旧是相对无力的;一项研究表明,有27%的小学生会偶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旷课。但是了解儿童看中学校哪方面的品质,至少可以告诉家长,如何替自己的孩子择校。更为根本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对孩子自己心中的利好都不闻不问,又怎么能说我们的学校是为了孩子好呢?
电影《造梦之家》(2022)剧照。
要是问孩子,校园生活如何,学校里什么最重要,一个最为稳定的回答就是—友谊。如果学校里的老师同学都很友善,他们在班级里也有安全感,那这样的孩子会是最幸福的。孩子非常重视安全感,反之,校园霸凌会让他们感到拘谨难过。校园霸凌现已成为最突出的,也是被报道也最多的一个问题;当被问及校园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时,霸凌也是孩子经常提到的一个词。
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有22%~29%的初中生在近一年内遭遇过某种形式的霸凌,导致他们担惊受怕,倍感焦虑。 霸凌行为有很多种形式,其中包括肢体暴力(在表明受到霸凌的群体中,有38%的人表示有人曾想在身体上伤害他们),但最常见的还是言语暴力、骂脏话以及“调戏”(teasing)。欧洲的一项研究发现,男孩和女孩有同等程度的霸凌倾向,但是男孩更可能使用肢体上的方式。研究发现,不仅欧洲如此,校园霸凌是很多都存在的严重问题;比如在蒙古、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发现,孩子不仅会被同龄人霸凌,同时也会被老师和其他教育从业者霸凌。小孩子可能不会专门提霸凌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对于自己和其他孩子得到对待时的公平性非常敏感,报告说别的孩子被老师忽略或被老师不公平地对待时,他们会感觉不舒服。
父母和孩子一样都有对校园霸凌的关切;全球范围内,来自父母的关切也越来越高涨。一项研究调查了欧洲范围内上千名家长,对于很多被调查者来说,校园霸凌是一个引发他们焦虑的问题;而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霸凌则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切点,这些地方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霸凌是个关键性问题。
作为回应,很多学校都有明文规定来处理学生间的关系。在英国,什么是应有的良好表现,应作何奖励,以及教工和家长在霸凌问题上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都是写在学生行为准则里的。换个角度说,学校也可以在全校范围内鼓励积极的社交互动。其中一种是在英国很流行的“圆圈时间教学法”(Circle Time),其目标是促进积极的社交互动,让孩子在几个环节中分组行动,以此培养良好的校园风气。孩子要学会各个环节的基本规则,他们会讨论到自己的利益和积极体验,然后开始帮助身边的同龄人。
类似地还有戴安娜奖(Diana Award),这是依照威尔士王妃戴安娜的意愿而生发出一项慈善遗产:年轻人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好。该奖项开创了一系列培训项目,比如关注并力图改变英国校园霸凌的反霸凌大使项目(anti-bullying ambassador programme)。戴安娜奖的方已经培养了超过24500名年轻人来解决校园和当地社区的霸凌问题。其他的一些全校参与的方法则更直接地关注暴力行为本身,比如在许多的小学里面流行的“行为修复计划”(Behaviour Recovery),要实际地解决一些常见问题,其中就包括扰乱课堂秩序以及课间暴力冲突的问题。
另外还有“伙伴制”(buddy system)这样的方法,可以舒服。父母和孩子一样都有对校园霸凌的关切;全球范围内,来自父母的关切也越来越高涨。一项研究调查了欧洲范围内帮助有困难的孩子发展良好的人际网络。以上的措施都可以表明,这些在很多中和语境下业已成为焦点的人际问题,校方其实一直都在解决。
要了解孩子们想从学校得到什么,另一种方式就是让他们自己设计一个学校。在一项研究中,科研人员与几组英国的小学生合作,帮助孩子们讨论、设计并绘制了他们理想的学校。他们最想要的东西,就是能够在学校以有趣的方式学习。
尽管他们希望学习能有趣起来,但孩子关于学习本质的观念反映出了他们当前的校园生活,比如,一个孩子设计出了“沙滩学校”,因为在室外学习更好玩。然而,这个沙滩是作为“不得不学习”时的一种调剂。另一个孩子干脆不要学校了,画中孩子们独自坐在安静的沙滩上,膝上放着笔记本电脑。沙滩静谧安逸,孩子们通过电脑学习,小测验会出现在孩子的屏幕上,测试结果会即刻上传给政府。这些受访的孩子就读于英国一所强调课程标准化考试表现的小学。另一个孩子的新式学校是一个“糖果工坊”,所有的活动都围绕巧克力展开。一台中央电脑通过虚拟的巧克力来测验孩子分数学得怎么样。在糖果工坊里,学习说出正确的答案的孩子将获得一块巧克力作为奖励。这种通过重复正确答案来获得奖励的模式,在很多其他孩子的作品中也有展示(奖励当然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没有一个孩子认为,在他们设计的户外活动或操场活动中也需要有这种奖励。孩子想象的学校是个可爱的地方,但是他们明显地区分了学校中的“学习”(learning)活动与“好玩的”(fun)活动。
这也不足为奇,孩子对学习本质的看法,常常反映出他们自己的学习经历。孩子如果经历了非常传统的教育(比如说,处于被动地位,只要简单地学习或吸收信息),那他就会把这种教育理念带入他理想的好学校中去。而有其他经历的孩子,比如那些支持孩子独立开展研究的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孩子,可能就会创造出其他更具互动性的学习模型。与其将自身视为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这些孩子更愿将学习看作一个主动的过程。老师可能最初只是提供一个问题或者目标,但这些孩子就会想要通过观察、探索和实验“把事情琢磨清楚”。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2004)剧照。
父母同样也极大地影响着孩子的认识论观念。大规模的亲子调查发现,父母的认识论(亦即对知识和学习本质的观点)影响着他们的教养方式,进而转换成孩子对于“何为知识”与“如何学习”的看法。比如,如果有家长鼓励孩子通而这种对考试结果的强调,无疑也影响了孩子对当前学习目过提问和讨论的方式来促进对问题的理解,那么相比不这么做的家长,他们的孩子的推理能力更有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相反,如果家长喜欢立规矩,强调控制和行为上的服从,那么他们的孩子就不太会把学习和知识看作一种探索。个人的认识论也与大量的其他因素互相影响,比如说它会影响对性别、社会阶级以及残疾的看法;举例来说,孩子问父母一些关于事物工作原理的问题的时候,小孩子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父母的答案的影响。然而,这种互动对男孩和女孩来说未必是“平等的”。不仅家长更期待男孩会对科学产生兴趣,而且一项基于博物馆的调查表明,人们为男孩解释科学互动展品的意愿,是为女孩解答的意愿的3倍。
对父母来说什么最重要?
当然,说到教育,尤其是说到孩子该去哪所学校、该接受何种授课方式时,要是觉得孩子自己“最知道”,那可太幼稚了。前文已经说过,孩子会受到教育方式和父母的巨大影响,所以很难让他们自己来评价什么是好学校、什么才是有效的教学(对任何年龄段的人来说也一样)。尽管听孩子的意见很重要,也应该照顾他们在学校时对安全感和支持的需求,但是这些必须与家长的意见相结合,因为家长才有权最终决定自己孩子的教育。
对家长来说,教育中最重要的东西源自他们自身对各种因素的考量,比如他们的文化背景、对孩子的社会期望、他们的认识论、他们对优质教育的设想,以及他们对力所能及的各种选项与信息的评价能力。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之间各有千秋。然而总的来说,在何为最重要这个问题上,父母们出人意料地还真有很多共识。一项覆盖11个的研究发现,父母最关注两件事:一是学校能不能提供安全又愉快的环境给孩子,二是学生的学业成绩好不好。研究还发现,当父母认为学校环境质量特别重要时,孩子往往会在学校表现得更好。
父母对孩子学业成功的渴望,源自这种成功所带来的长期效益。整个欧洲的父母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从教育中最想得到的,就是教育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流动性的前景,好让他们的孩子过上好日子。然而,自身学历极低的父母,以及孩子的社会轨迹尤未可知(比如正在经历贫穷和困境)的父母,他们也许是最怀疑教育可能带来社会流动性的一批人。有两样东西往往是相关的:父母对教育给孩子生活“带来”的裨益有多少期待,他们就会有多积极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之中。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2004)剧照。
在决定孩子该在英国国内读什么学校的时候,对家长来说,学校的三种特质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学校的教学质量,生源的社会经济组成,以及家校之间的距离。”这就意味着,比方说,大部分的英长都会选择教学质量更好、贫困家庭学生更少的那些学校。所以,他们能接收到的学校信息,对他们的选择有着强烈的导向作用。在英格兰,这些信息可能来自公开发布的学校评测结果,也可能来自学校的宣传。然而有几份研究发现,择校范围不变的情况下,贫困的家庭有可能选择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而离家近是影响这一决定的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这就导致英格兰的公立学校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学校都是以生源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的。
有一种被称为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的教育运动想要挑战这种现状。这项运动响应了联合国的“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目标,对全球范围内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机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源于对儿童权利的信念和共识:“不论孩子在身体、智力、情绪、社交、语言或其他方面的条件如何,所有孩子都有一同接受教育的权利,而这种接纳才能创造良好的教育观念和社会观念。”
许多都签署了这项共识,并创造了众多政策措施,以期实现教育机会公平,确保没有孩子被落下。很多欧洲同时也是《残疾人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的缔约国,公约第24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应当确保在各级教育实行包容性的教育制度和终生学习。”世界范围内的全纳教育,被视为对全体儿童开展教育的一种响应,接纳任何社会背景、阶级和身心状况的孩子。比如,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上民族最多样的,其政府有明确的目标要给予所有孩子至少九年的基础教育,而且正在发展全纳式学校来实现这一目标。
父母们谈到全纳教育,最常提出的一个话题就是,孩子在班里能学得多好,特别是当班里有些孩子有特殊教育需求和残疾(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 disabilities,SEND) 的时候。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如果先把一些孩子放到专门的特殊学校里去的话,是不是更好一些?
电影《造梦之家》(2022)剧照。
首先,如果孩子有学习困难或者感觉损伤,那他们的父母就会面临这个问题。但这些孩子之间又存在着大量的个体差异,有的孩子只是识字能力有问题,但有的孩子无论年龄多大,无论经历了多少事情,他们的智力水平、人际发展和沟通能力一直都停留在初级阶段,几乎所有活动都需要他人帮助。根据的认定和政策,这样的孩子大约占了孩子总数的15%左右。
其次,即使孩子不符合前一组的定义,父母依旧要考虑特殊需求和残疾的问题。在很多,有特殊教育需求和残疾的孩子是一个被非难的群体,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他们待在一起,也不想让孩子和他们上一样的幼儿园和学校。全世界的教师和教育家都报告说,有些家长不想自己的孩子在受教育的时候,身边有任何“怪”孩子,任何形式的“怪”都不行。新西兰一家早教中心的主管告诉研究者:
一些家长对这事(残疾)非常有偏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见到这些。他们可能非常残忍……他们会把孩子拽出来,因为有些孩子有残疾,他们不想自己的孩子看到这些。
在英国,老师反映一些家长会表示,“要么他走,要么我带女儿走”。父母们总是觉得,如果学校或班级里有残疾孩子或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那自己孩子的教育进度也会受拖累。
然而研究表明,如果同龄人有特殊教育需求或残疾,和他们在一起的正常孩子会更积极地对待这一群体,也更愿意和他们一起玩。
对一些家长来说,这是个好结果;对另一些来说,这种结果不该出现。现在就有了这样一个局面:尽管人们大力推行全纳式学校,比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的35个成员国中就是如此,但是对于家长来说,这种“来者不拒的学校”(schools for all)的成绩和后续社会影响,依旧是个饱受争议的关键议题。
总体来说,大样本量的研究并没有发现被放在(专门的)特殊学校的有特殊教育需求或残疾儿童在学业上有什么优势,而1300份研究的证据表明,全纳式学校的积极效果微乎其微。一些研究关注了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群体,尤其是对课程内容有要求的群体,考察了他们的教育结果,发现实际情况与前文所述不太一样,而且更加复杂;比如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在普通学校和特殊学校都能进步,但是语言和交流技能在普通学校里发展得更好。
大量研究发现,当班级里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的比例在10%左右时,这些特殊的孩子都能取得积极的或者中性的发展结果。所以,在为孩子选择学校的问题上,研究结果是比较支持(当然不会指责)全纳式学校的。这些研究反映的是孩子间、学校间以及各校教学质量间的个体差异,更仔细地揭示了现实情境,而不是简单地比较学校的编班配置和教育成果。
优质的教学是什么样?
父母觉得孩子该怎么学习,很大程度上指导着他们支持孩子学习的方法,以及他们希望校方和老师如何工作。但很多观念本质上就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说,在《教育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Education)一书中,马丁·朗(MartynLong)及其同事就发现,父母在“教学中什么最重要”这个问题上有三种相左观念。他们发现,父母都各有说辞:
1.“课堂规模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教学质量”或“缩小班级规模明显可以提高学校成绩”;
2.“孩子们的老师是教育中最关键的因素”或“老师其实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孩子自己的知识和动机”;
3.“严格的规矩和惩罚在调教问题行为时至关重要”或“积极的行为来自于他人的示范,惩罚没用,只会让孩子自己变得残忍”。
由于儿童的教育经历本质上就很复杂,所以也很难完美地解决上述问题。那么基于这种复杂性,马丁·朗转而回顾了全球范围内与以上述每一种观点相关的文献证据。他的结论是,在对照实验中,缩小班级规模确实可以提高孩子的学习成果,不过也没有提高太多;更重要的是教学手段的改变,其影响也更加明显。同时他也发现,长远来看,惩罚并不是个高效的策略,也不会帮助儿童学会正确的行为方式。最终他认为,教师是影响小孩子学业成绩的最关键的积极因素,但相较于儿童的家庭背景,教师的影响还是有“太多”的变数。
前文说过,父母的认识论观点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孩子该接受何种教育,哪些班级活动在教育上是有价值的。同样地,教师对“孩子该如何习得知识”的观念,也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教学方式—这就影响了老师和父母会如何界定“优质的教学”。所以重点不仅在于课堂中的手段,更在于指导这些手段的观念,尤其是关于儿童如何学习的观念。
吴淑真(Shu-Chen Wu)和尼尔马拉·拉奥(Nirmala Rao)比较了德国和香港幼儿园教师的观念,她们问了这些老师一系列问题,而老师需要回答强烈同意、同意、不同意也不反对、反对或极其反对。她们发现在学习与玩耍的关系上,两组老师有一些非常不同的看法;比如,在对以下陈述的态度上就很不一样。
·孩子们玩的时候,老师在场会让他们学得更好。
·玩的时候,通过老师的指导孩子们会学得更好。
·老师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孩子的游戏中。
相比德国的老师,中国老师对每一条观点都更加偏向于同意;而德国老师则不赞成给出的大多数的观点。中国的老师没有看到孩子对“自由”玩耍的需求,或没有提及这种需求。他们认为,自己作为老师应该去指导孩子的游戏,使游戏具有其应有的教育意义。我们曾讨论了中长对游戏的态度,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力;而在教育体制内,我们也可能观察到同样的影响在发挥作用,甚至让玩耍成了“学习的对立面”。相反,德国幼儿园教师的观念可以说是反映了皮亚杰派的观念,影响着他们在教室里的行为方式。正因他们相信,孩子需要通过探索和游戏来学习,所以他们促进学习的方式是提供“自由”的玩耍时间,给孩子提供游戏的器材,好让他们觉得有趣。他们认为,这些活动有利于儿童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
其他的一些国际性研究发现,教师对这些教学手段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冰岛和澳大利亚的老师更支持建构主义的观念,而马来西亚和意大利老师的观点则更融合,往往对建构主义和直接传播法都很认可。
教师针对有关认识论问题的看法,也能反映出他们在课堂中的实践;一般来说,采取传统教学方法的老师在全纳式或多元化的班级中,其教学手段一般不太灵活,效率也不会很高。然而,要指出哪种理论“最好用”,这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不同文化、不同语境之间的变数实在太大,而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标准也各式各样。
全球范围内的研究认为,如果各国想要提升教育质量,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要在教师培训阶段吸引并支持有天赋的教师。但是,关于教学方法的本质依旧众说纷纭,而且这也是与文化因素息息相关的;比如说,韩国的小学生在学业水平上远超其他的孩子,但其背景是孩子“在巨大的、残酷的压力下努力着。天赋不重要—因为他们的文化相信,努力和勤奋高于一切,人人都没有失败的借口。孩子全年都在学习,要在学校学,也要跟辅导老师学”。
童年是用来学习的时光,而如何学、学什么、为什么学则是孩子生活中的关键层面。所以也难怪,教育会成为父母和教育政策制定者的一个雷区,尤其是教育中还有那么多选择、那么多相左的观念。在“如何择校”和“教育的关键”两个观念上,父母被几个因素引导着,其中就有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他们的野心以及他们对学习发生方式的见解。父母会相应地做出不同的选择:孩子该去哪上学?孩子的受教育方式会不会让他们满意?但是其中缺失了一个声音,那就是孩子自己的意见。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2004)剧照。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教育研究中,孩子自己的态度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他们喜欢去什么样的学校?他们看重学校的哪些品质?即使偶有讨论,他们的意见也很少被付诸实践。现在明明白白的一点是,父母和孩子都希望学校能提供安全和幸福感,但是父母还想要学校提供学业成功、社会流动性以及远在未来的成就。他们希望学校既能帮孩子立刻社会化,又让孩子为将来做好准备。对于孩子、父母和教师而言,这其中有个微妙的平衡。
本文选自《为人父母:那些证据告诉我们的事》,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英]维多利亚·库珀 [英]希瑟·蒙哥马利 [英]基伦·希伊
摘编/安也
编辑/商重明
校对/卢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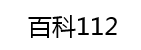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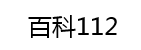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吉祥麻将开挂神器下载”(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吉祥麻将开挂神器下载”(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