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作家群中,贾平凹以其优秀的写作能力不断活跃在文坛中,平均两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效率也让读者和评论家门看到了这位马上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作家惊人的创作力和活力。贾平凹不止一次称自己是个农民,其作品也在不断表现着对传统乡土与文化的守望姿态,乡土与乡土文化滋养着贾平凹的作品,同时他的作品也从历史纵向的角度和现实的横向角度为中国农民构筑了一部部壮丽史诗,从改革三部曲到《秦腔》甚至其创作的都市题材小说都有着”农民“的影子,贾平凹对农民形象的刻画和展现也始终跟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历史的洪流中农村与农民的真实状态以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
纵观电影百年发展史,由文学改编的电影占据半壁江山,但对高产作家贾平凹作品的改编仅有四部,有趣的是,这四部改编作品中塑造的农民形象却巧妙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新“农民形象的变迁与生成。《高兴》是贾平凹以自己的朋友为原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也文学史次表达了对城市中拾荒者的命运的关照,在残酷的现实下展现拾荒农民的城市梦。
2009年,导演阿甘将这部作品改编成同名喜剧电影,在基本剧情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削减原著喜剧背后的悲剧性,加入歌舞元素,讲述了刘高兴与五富进城工作,误打误撞下开始拾荒,在城市中刘高兴收获友情与爱情,并以五富起死回生、孟夷纯无罪释放、高兴成功融入城市的完满为结局。
一、 “飞机”符号与城市认同
刘高兴不同于传统农民,他对城市有着纯然的认同感,这样的认同意识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电影里都通过各种符号的外延映射出来。在小说中,刘高兴的肾先一步移植到西安一个大老板身上,肾的移植使刘高兴从身体到精神上产生了对西安的归属感,从而坚定地认为,“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肾作为刘高兴身体的一部分先于他个体被城市接纳,肾的召唤也成为刘高兴进城的动机之一,的移植也让刘高兴产生了血肉联系下对城市的认同。
而电影中,飞机符号替代肾符号成为刘高兴城市之旅的精神支柱,这样的符号选择既是追求影视视觉冲击力的结果,也是将刘高兴对城市的血肉认同向精神认同的转化。任何物都是一个“物-符号”双联体,它可以向纯然之物一端靠拢,完全成为物,不表达意义;它也可以向纯然符号载体一端靠拢,纯为表达意义。
飞机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在一般语境下仅为纯然之物,并不表达任何意义,而电影中,刘高兴在前往西安城的大巴上放飞手中的遥控飞机时,飞机便成为一个符号携载着刘高兴造飞机、当飞行员的理想和走出大山、成为西安人的城市梦,而这样意义的赋予也在随后刘高兴与五富之间的对话中更显明晰,五富的理想是进城赚钱,城市只是他暂时的目的地,而当五富反问刘高兴关于理想,特写镜头下刘高兴向车窗外放飞电动飞机,飞机携带着他的理想飞到大山之上,而飞机也被赋予了刘高兴的理想含义,飞机不仅是理想的能指也是其所指。
雅柯布森指出,一个符号文本同时包含这六个因素,当符号表意侧重于对象时,符号出现了较强的“指称性”,或称“外延性”。此时符号过程明显以传达某种明确意义为目的。当刘高兴在城市意图通过拾荒融入城市的时候,依旧不忘记自己的造飞机、当飞行员的理想,电影符号的内涵与外延是有机的对立统一,内涵是外延的前提,外延是内涵的放射,飞机符号在电影中将刘高兴对城市的追求与认同变成具象地在城市上空飞翔,而这样的转化也使飞机增加了其成为“人上人”的梦想的意蕴。电影的结尾刘高兴实现了自己的飞机梦,融入城市的同时做了一回“人上人”,飞机上五富吐出的呕吐物全然落在忘恩负义的老板韦达头上,五富也在这次飞行之旅中死而复生。
二、“红色女士高跟鞋”与爱情隐喻
从象征城市的皮鞋、象征农村的烂鞋、胶鞋与布鞋以及蕴含刘高兴城市梦与爱情梦双重隐喻的高跟尖头皮鞋,有关“鞋”的符号建构在小说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而在电影中,高跟尖头皮鞋具象化为红色女士高跟鞋,成为刘高兴爱情梦的象征。“世上的好多东西都是一个引逗着一个的”,刘高兴自诩城里人,在他心中只有穿高跟鞋的女人才配得上自己,而那双买给未来老婆的高跟鞋就像有了茶壶配茶杯一样,成为招老婆的信物。电影符号的外延层次来自符号的社会性,以整个社会的认同或“契约”和集体潜意识为基础,高跟鞋在社会潜意识中既是女性的代表,也是现代文明下的摩登产物,高跟鞋符号建构在进城务工单身汉的角色设定中拥有了“爱情”的外延性意义。
而意外地去按摩店收破烂的过程中,暖红色色调下,中景镜头中刘高兴随着楼梯小心翼翼上楼,随之以刘高兴脸部表情为背景楼梯上忽然出现的高跟鞋为前景,在对红色女士高跟鞋的特写镜头下,高跟鞋符号的外延意义得到具象化呈现,而高跟鞋符号的爱情意味进一步形成孟夷纯的解释项。按照皮尔斯的无线衍义理论,任何解释项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符号,新的符号又产生新的意义,以至无穷。但符号意义上无限开放,实际上不会永远延续下去,这个暂时停止就是意义的成形。
当高跟鞋的符号形成爱情外延意义,而爱情外延意义构成的符号又产生新的“孟夷纯”的解释项,这样的解释项在刘高兴精神上形成完美的闭环,孟夷纯就成为高跟鞋符号的意义成形,刘高兴作为高跟鞋符号的发出者,孟夷纯就是他意图上期盼解释的理想暂支点,于是孟夷纯便是高跟鞋符号的“意图定点”。红色是欲望的象征,代表着刘高兴内心炽热的爱,电影给予高跟鞋色彩,镜头语言下以浓重的色调和富有冲击力的形象使高跟鞋意象具象化的同时,其内含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升华。
三、“新”农民形象的生成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代以上是农民的俗语并非无中生有,而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在逐步富强的过程中,农村与城市的对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贫富差距、资源失衡以及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侵入是现实问题也是艺术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尤其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化解与相融,农民精神上随之生成的波动与变化也是贾平凹作品中所呈现的重要元素,从四部改编自贾平凹小说的影视作品看,其中的农民形象既有坚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有站在传统与现代分界线上的矛盾体,也有坚定走上现代化进程以科学科技武装自己的新式农民,而刘高兴的“新”首先便体现在对现代科技的认同。
与小说不同,电影中刘高兴将理想具象化为“飞机”,而飞机符号的外延不仅是走出大山的农民做“人上人”的飞天梦以及融入城市的城市梦,更是现代科技力量的呈现,刘高兴将梦想具象化为造飞机、开飞机,本质上是对现代文明与科技的认同,这也是现代文明对农民思想与精神上一次深刻的改造,对现代文明与科技的渴望是刘高兴不同于以五富为代表的传统农民之“新”。
其次,“新”农民之新不在于向城市的靠拢与对传统与农村的抛弃,而是从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对刘高兴而言,进城后“混好了就不回来了”,其本质是对现状的不满足从而去往新的更好的地界找寻更优质的生活,离开家乡去往城市是手段,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才是目的,影片最后飞天梦的完成也预示着,这些进城务工人员想要融入城市也并非是难以实现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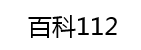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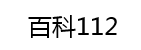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填大坑游戏可以开挂吗”(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填大坑游戏可以开挂吗”(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