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生还者》根据同名游戏改编,剧情设定与后疫情世界的现实状况不谋而合,播出后获得了极高口碑。(资料图/图)
想象一下,如果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某种真菌基因突变、进化,迅速在全球蔓延,像病毒一样感染每一个活着的人,进而占据他们的大脑,控制他们的行动,使其完全变为攻击他人的怪物——最重要的是没有药物,也没有方法,你将会怎么办?
在游戏《最后生还者》中,主人公乔尔和艾莉便生活在这样一个末日世界中。为了保护免疫者艾莉,乔尔带领她踏上冒险之旅。从陌生人到“父女”,游戏之外有关末日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议题,引起人们的思考。
2013年6月,顽皮狗工作室在PlayStation推出这款游戏后,引起极大反响,拿下了当年游戏界金摇杆奖的最佳故事剧情奖。2023年1月15日,在游戏发行十年后,由它改编而来的剧集《最后生还者》季在美国首播。截至3月中旬播完,它的IMDb评分超过9.0,豆瓣评分9.1。BBC甚至评价它为最好的游戏改编影视剧。
这种由游戏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并不少见。1993年,任天堂的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便被搬上大银幕,这是游戏影视化的新尝试。遗憾的是,它并未取得成功。口碑上,IMDb评分仅为4.1;票房上,电影投入的预算超过4200万美元,但全球票房收入只有3890万美元。主演鲍勃·霍斯金斯甚至认为在此剧中出演,是他做过最糟糕的事情。此后三十年间,动作冒险类的《古墓丽影》《刺客信条》,生存冒险类的《寂静岭》《生存危机》,格斗类的《街头霸王》等游戏陆续改编成影视,但大部分口碑都一般。
这一次《最后生还者》的改编显然是个新转折。相较于其他游戏改编而来的影视剧,《最后生还者》究竟做对了什么?
“我只是选择了一个故事最好的游戏”2013年,在游戏《最后生还者》发售的这一年,游戏界基本上还是以开放世界角色扮演游戏为主导,例如《侠盗猎车手》《上古卷轴》等。在这类游戏中,玩家可以只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任务。在一些有分支剧情的游戏中,玩家的行为选择还会影响剧情走向。
《最后生还者》的创作者尼尔·德鲁克曼也被如此要求过,但他拒绝了。他认为,主人公乔尔作为一个拥有暴力一面,也拥有温柔一面的人,是不会做出某些抉择的。在他看来,如果玩家可以自由做决定,那么会破坏乔尔这个角色的性格和行为逻辑。从当时游戏的创作环境来看,选择一种坚定的线性叙事似乎有些冒险,但游戏推出后收获的奖项和评价证明了这样做的效果。
在游戏中,乔尔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单身父亲,在疫情暴发初期失去了他的女儿,二十年后他在波士顿的隔离区从事工作。他和伴侣泰丝,为了完成“火萤”组织首领玛琳的托付,开始了护送免疫者艾莉的旅途。在途中,泰丝被感染,为了保护乔尔和艾莉,选择独自留下来抵抗追击者。乔尔也渐渐在和艾莉的相处中,将她当作女儿看待。
末日世界的图景、主人公关系的发展变化、末日社会中人类如何生存等思考融汇在同一个文本中,使它拥有大多数游戏都无法达到的特殊厚度,而这又刚好与影视改编所需的故事性及更深层次的人性议题相契合。《最后生还者》编剧之一克雷格·马津也说,“我只是选择了一个故事最好的游戏。”
1993年,在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上映前,人们或许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游戏文本和影视文本的巨大差别。在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中,水管工马里奥拯救公主更多的只是作为一个背景设定,整个游戏更偏重于玩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水管工从头到尾都在一蹦一跳,也依然可以吸引大批玩家。
影视剧则不同,最吸引观众的始终是剧情。在电影改编中,原本游戏的背景设定成为了主线剧情:意大利裔水管工马里奥兄弟,为拯救公主黛西,在异世界与邪恶首领库巴产生对抗。在辅文本转为主文本的过程中,编剧必然需要在主线剧情之外,几乎“另起炉灶”来编写故事,并使它变得更丰满。两个文本之间的联系变得很弱,几乎只剩下一些相似的游戏场景和部分设定,难免将改编往滑铁卢的方向推进。
在这之后,一些游戏改编又走向了相反的极端:过于看重对游戏文本的忠实性,甚至连一些游戏视角都极尽可能地还原。比如《毁灭战士》,这部电影为了突出人称射击游戏的特点,甚至用了五分钟时间,模拟主角的视角。整个画面的动作,如在走廊里行动、用枪击倒敌人等都是通过这种视角来呈现的,观众只能看到画面底部主角的手和武器。对游戏玩家来说有沉浸式体验感的视角,对电影观众来说,却显得很有局限,难以接受。
事实上,游戏着重玩家的体验感,讲究的是互动性,游戏文本的创建更多的是为玩家营造一种沉浸式氛围,玩家即角色本身。而影视文本更强调情感的共鸣,共鸣本身就意味着观众与角色是有距离的,依靠文本,这种距离可以逐渐弥合,但难以做到完全重叠。
《寂静岭》做出了游戏改编的优秀示范。2006年,改编自同名游戏的恐怖电影《寂静岭》上映。影片对游戏的世界观及叙事结构没有做大幅度的调整,游戏为影片的改编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文本。
游戏的主干剧情并不复杂,主人公哈里带着女儿到寂静岭度假,半路女儿离奇失踪,他踏上寻找女儿的旅程。在此过程中,他也逐渐揭开隐藏在寂静岭世界中的重重迷雾,悬念感与恐怖感始终笼罩在周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游戏在宗教神秘主义的浓重氛围下,还涉及对亲情内核,以及正义与邪恶议题的讨论。也因此,整个故事在改编成电影时,更具有引起观众共鸣的深层基础。
同样地,《最后生还者》除了在基本故事上,牢牢把握住乔尔和艾莉从形同陌路到建立起父女情感的主线,还通过他们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探讨在末日社会中人类如何生存的问题。是像乔尔那样帮助别人,还是像某些掠夺者一样,在人类社会内部互相攻击,又或者只是当一个冷漠的末日幸存者?这些思考都无形中提高了《最后生还者》改编成功的几率。

在末日世界,主人公乔尔在护送免疫者艾莉的旅途中,二人形成了父女般的亲情。(资料图/图)
改编越大,越需要在情感上证明年初,当《最后生还者》的编剧克雷格·马津和尼尔·德鲁克曼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改编。在游戏中,暴力和动作的戏份让玩家在通关时更具代入感,但是,当介质发生变化,编剧们需要思考的是如此多的动作情节在改编中应保留多少。
尼尔·德鲁克曼更想让游戏中的暴力情节能刺痛人心,而非激起兴奋。对此,克雷格·马津认为,在游戏中,当玩家杀死某个人时,对方更多的是被理解成一个障碍物,而非一个“人”。在剧中,他们更想让观众能够体会到,死亡的是某个活生生的人,而非仅仅是屏幕上的某个像素点。
在这种思考下,编剧们在改编的剧集中并没有用大篇幅的笔墨去还原太多动作戏份,而是进行了针对性的删减。“乔尔躲避子弹的技巧并不重要。”克雷格·马津说,他认为,以往游戏改编多次出错的原因是试图完全还原游戏中的动作。
剧中最大胆的改编出现在第三集。游戏中,比尔和弗兰克的感情是含蓄克制的,并没有明示出来。比尔住在一个废弃的小镇上,他的同伴弗兰克因感染自杀。在那之前,弗兰克受够了比尔的冷漠和唯我独尊的态度,准备抛弃他,逃往波士顿隔离区。在弗兰克自杀的房间里,比尔发现了他的尸体和他留下的遗书,一瞬间,难过与愤怒的复杂情绪涌了上来。
讨论这场戏时,尼尔·德鲁克曼最初认为要把游戏里的一些动作场景还原,比如在乔尔被装置吊起来之后,艾莉帮助他将绳子割断等。但克雷格·马津则觉得,有意思的应该是比尔和弗兰克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这一点应该继续深挖。
在以往游戏改编的影视中,例如《古墓丽影》和《生化危机》系列都在电影中保留了相当多的动作戏份。显然,相比于在角色塑造及叙事方面花的功夫,导演和编剧似乎更加注重场面的刺激和好看。但这两个系列在之后的续集中,大幅度的动作场面已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观众对人物的塑造和剧情的发展提出更高的期待,以至于到系列终章时,影片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诟病。
回到《最后生还者》剧集,改编后的比尔和弗兰克作为伴侣一起生活了近二十年。剧中对他们共度的二十年中重要节点都详细地铺展开来,讲述他们如何相识和相爱。比尔最初独自一人居住在废弃小镇,他在周围设置了很多陷阱,防止感染人群和其他不友好的人进来,弗兰克在前往波士顿隔离区的路途中掉进陷阱,被比尔救起,而后两人相爱。
实际上,第三集的改编抓住了“爱”这个核心概念。尼尔·德鲁克曼的改编心得是,与游戏偏离越大,就越需要在情感上证明自身。比尔原本是一个冷漠的末日生存者,他的爱只针对特定的人;而弗兰克则是一个浪漫热心、充满关怀的人,“关注身边的事物,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他说。
在弗兰克的影响下,比尔渐渐有了一些改变。他们种草莓、种花、翻修镇上的一些商店,展现了另一幅末日社会的生存图景。在饱受疾病折磨后,弗兰克想让比尔帮助他自杀,而比尔也因为爱,最终选择与弗兰克一起殉情——这样“浪漫”的举动在遇到弗兰克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末日社会中,绝望的情绪像感染者身上滋生的真菌一样四处蔓延,一部分人也因为自己的利益到处杀伤抢掠,人类社会不仅在外部遭遇生存的威胁,也在内部进行自我瓦解。当观众被拉入比尔与弗兰克的故事里,他们也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当末日来临,自己要如何抵抗对未知及死亡的恐惧?
比尔和弗兰克之爱,毫无疑问,给观众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无论是比尔那种有限定性的、狭义的爱,还是弗兰克对周围事物广义上的爱,在末日社会的绝望中,这种珍贵的情感都给予人们温情的慰藉,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当末日来临,爱也可以成为人类抵抗死亡恐惧的一种方式和力量。
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嫄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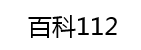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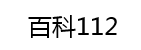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大眼四川麻将怎么知道别人开挂”(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大眼四川麻将怎么知道别人开挂”(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