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用:人类最宝贵的工具?》,[德]米歇尔·霍华德 [德] 卢西亚诺·帕罗迪 主编,温亚男 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
如何定义无用性?
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无用性,但我越是试图给它下定义,它就越发无迹可寻,令人难以捉摸,特别是当这种尝试被投射到一个特定的对象或现象上面时。对某个特定对象最具代表性的无用性的每一次探索,都会赋予其新的可能性,而为破译和定义无用性而采取的每一步措施,似乎只会增加其价值和揭示出更多的附属属性。在仔细审视的过程中,无用的东西总是会无一例外地在某一时刻激起人们的感知倾斜,其不可言喻的价值变得令人无法忽视。

《无用:人类最宝贵的工具?》内页插图。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他的哥特式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Gray)的序言中首次提出“一切艺术皆无用”,自此,这一主张在围绕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争论中被反复引用。1890年,一位崇拜者写信给王尔德,请他解释这一句话的意思,他回信说:“艺术作品是无用的,就像一朵花是无用的。一朵花为了自身的喜悦而绽放。我们则在观赏花时获得片刻喜悦。……当然,人可以卖掉这朵花,这样花对他就是有用的,但是这与花本身没有任何关系。这并非其本质的一部分,而是非本质的,是一种误用。恐怕我说的这些十分晦涩,但这一主题是很深刻的。”奥斯卡·王尔德总是如此,一个乍看起来像是纯粹基于美学和智慧的解释,实际上是对更深入的洞察力的主张和对社会认知的挑战。在他写这封回信的当时,在社会认知中,鲜花绽放的最大作用就是繁殖。
早在1735年,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出版了《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在该书中,他首次尝试通过分类来赋予自然界“秩序”,并建立了双名法体系。在该体系中,生物的名称由一个属名和一个种名组成,属名在前,种名在后。这当然有效地满足了我们对知识的渴求,但它也意味着描述的胜利,尽管这种描述是相对原始的。可以说自然界的“分类”预示着后续价值分类的变化。瑞安·史泰克(Ryan Stec)展示了描述体系如何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感知并且丰富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因此,当奥斯卡·王尔德说花儿为自己的喜悦而绽放时,他并非对花的繁殖一无所知,相反,他强调的是开花这一自然“魔法”本身的价值,并告诫我们当事物的秩序被揭示时,要警惕好奇心随之丧失的危险。
迪德希·迪德克森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说“从魔法中解放出来的知识会摧毁世界(而魔法本身远没有这么危险)”。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认为,任何现象或物体的无用性都取决于我们知识的匮乏和我们用来摆脱无知的手段的原始性。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在《走向新建筑》(VersuneArchitecture)中谈到了“原始人”的概念: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无用性,只有对人类无用的资源。

《无用:人类最宝贵的工具?》内页插图。
用无用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
王尔德对看似无用的事物的关心可能源于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庄子的影响。在撰写那篇序言时,他正在研读庄子的作品。王尔德看到庄子作品的版英译本后,发表了名为《波迈的批评家》(A Criticin Pall Mall)的书评。他写道:“庄子一生都在宣扬无为而治的伟大主张,倡导用无用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
庄子喜欢用寓言说理,有一则寓言叫“无用之树”。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云游的木匠看到一棵巨大的老栎树矗立在田野。木匠对他的徒弟说:“这是一棵无用的树。如果用它做船,很快就会腐烂;如果用它做工具,又很容易毁坏。这棵树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当天晚上,他梦见这棵老栎树跟他说:“你为什么拿我跟你种植的果树相比呢?它们甚至在还没有开始结果的时候,就遭受刀劈斧砍。它们的枝条被折断,树枝被割裂。正是因为那些果树能结出鲜美果实,才常常遭受伤害,半途夭折。各种事物莫不如是。所以我很早之前就想变得一无所用了。最后,无用才成了我最大的用处。因为无用,我才能不夭斤斧,安享天年。”
大多数科学界人士现在终于达成一致,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新造林。这个关于造林重要性的一致意见是在用尽了一切其他方法,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的地球工程之后才达成的。实施地球工程提案从起初看似无害的,如人工降雨,到存在很大问题的,如向大气层注入巨大的火山灰云,甚至用反射膜包裹大气层来反射太阳光和热能。这些方法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尚不为人所知,但我们确实知道树木的巨大作用,并且自人类出现之初,它们就一直与我们同在。
事实上,它们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出路。例如:树木能将水从大海带到最遥远的内陆,因此,如果我们能将森林连接起来,就能让沙漠消失。最近,人们正在研究树木吸水的原理,以期能开发出简单经济的方法,来克服重力作用,向上输水。此外,许多研究表明,树木和森林越是不受人为干预地自由生长,或者说,我们越是放任它们,它们在对抗气候变化方面就越有效。实际上,如果我们任其自由生长,即使最后只长成了枝杈横生的矮树丛也比商业化的森林更能对抗气候变化。因此,无用之树不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同样也会保全人类的存在。

《无用:人类最宝贵的工具?》内页插图。
哈瑟利认为,经典英伦户外景观——柔软起伏的草地山丘上点缀着小树林和灌木丛以及偶尔出现的装饰性建筑——形成的真正决定因素,是这些景观的设计意图就是让人们远观而非亵玩。人们可以沿着碎石路悠闲地漫步其中,享受其广阔的空间,这与许多现代景观设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正是这种非常英式的户外空间的无用性成就了贵族的豪华庄园和20世纪住宅区。其中,罗汉普顿的奥尔顿庄园(Alton Estate)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杰作,它实际上坐落在一个由18世纪欧洲最著名的景观设计师能人布朗(Capability Brown)设计的花园。这种坐落在乡村连绵起伏的旷野中的住宅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政府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之一。那些住宅区如果得到了良好的维护,至今依然十分宜居。如果作为公租房,政府就会承担起维护的责任,那么保持宜居的状态就丝毫不成问题了。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想到了一个“两全之法”——既破坏这一遗产,又能确保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为保守党人赢得投票。她提出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购买权计划》,使租住政府公租房的人有机会以底价购买该房,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一计划,(事实上,在关于该计划的广播中,她使用了“house”(房子)一词,尽管数百万租户实际上住在公寓(apartments),这本身就是对“住宅区”的控诉)。自然,众多人占了这个计划的便宜。然而,由于缺乏针对公共空间——如通往公寓的小路或环绕公寓的绿地——的归属的规章制度,这些小路和绿地很快就无人照管了,这些宝贵又古老的充满英伦风情的无用的户外空间也很快就不受欢迎了。
英国贵族花园的地标往往是古怪而愚蠢的建筑。愚蠢(Folly)一词源于法语词Folie,这个词既描述了疯狂,又形容了奢侈,用它来形容主要为装饰和地主阶级的享乐而建造的浮夸建筑,再合适不过了。但是,18和19世纪,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种植园中建造的愚蠢建筑并不都以享乐为唯一目的。在那段时间,连续的干旱和疾病使当地的租户变得穷困潦倒,他们想继续留在那就要向地主缴纳什一税,而且大多数是外居地主。建造这些愚蠢的建筑与辉格党政府为应对1846年的马铃薯饥荒而策动的公共工程计划出于同一种目的。当年的计划迫使爱尔兰饥民用工作来换取勉强果腹的钱粮。
在这些地主的心目中,建造公共工程可以使饥饿的阶级忙于工作,从而没有时间组织起来叛乱。不幸的是,由于长时间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切肤的饥饿人变得更加虚弱,繁重的劳动大大加速了他们的死亡。奇怪的是,这些建筑反而是现存最轻浮的建筑之一,后来被人们称为“饥荒之耻”。因此,正如卡塔尔当年为世界杯足球赛而精心设计的建筑一样。(建筑工人是移民,他们的护照被收走了,以防止他们半途离开),正是对社会正义的漠视最终产生了那些满足资本主义最黑暗力量的作品——实现他们占有无用之物的心。无用这个词直到1590年前后才出现在书面英语中,而对这个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200年前后,人们怀疑,这个近300年的空白不是仅仅缺乏书面记录而已,而是有更深刻的意义。

张伯伦花园,《无用:人类最宝贵的工具?》内页插图。
艺术是一种职业,
与其他任何职业没什么两样
Use(使用)一词的出现取代了古英语单词brucan,brucan与德语单词brauchen密切相关,它的本意是“享受”,这与我们目前对该词的功利性理解相去甚远。社会主义作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开创性的作品《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中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工业革命对我们文明中的许多关键词汇进行了意义上的转变,他特别挑出了五个词,回头来看,它们与use的含义从“享受”(一种极其公共的活动)到“使用”(一种个人主义的活动)的转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词是:Industry(工业;勤勉)——不再仅仅表示勤劳、勤勉等人类属性,而是成为表示制造业和产业的一个集体词;Democracy(民主)——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学术语,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它成为了一个政治用语;Class(班级;阶级)——不再是学校和学院中的一个部门或团体,而是指广泛的社会划分;Art(艺术)——不再是指技能,而是指想象力和创造艺术;Culture(文化)——根据威廉斯的说法,它经历了一系列更加复杂的转变:它开始是“自然增长的趋向,然后通过类比,引申为教养的过程”,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它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状态或思想习惯”,到19世纪末,它变成了“整体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智力的和精神的”。
Use从“享受”到“使用”的过程遵循了威廉斯描述的意义转变历程,即集体利益的概念(享受某种东西而不是使用它)被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所逐步取代。露丝·桑德雷格探讨了适用于白人男性资产阶级品位的无用性的新定义,她用惊人的事例讲述了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如何将艺术提升到无用性的高度,来掩盖其恐怖性。

电影《博物馆时光》(2012)剧照。
在那之前,艺术一直处于社会的中心。此外,直到18世纪末,艺术(art)、艺术理论(arttheory)或美学理论(aesthetictheory)这类名词还没有单数形式,而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艺术(arts)和艺术的规则手册(rulebooks)。此外,规则手册预设艺术技能可以通过教学掌握:艺术是一种职业,与其他任何职业没什么两样。
资本主义的发端助长了艺术家或雕塑家离群索居的观念:他们可以躲在自家阁楼,不受市场的影响,只遵循他们的职业使命和灵魂深处的力量。她认为:“审美自主性和无用性的出现终于派上了用场——声援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使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等级制度分化合法化,这是当时新的资本主义秩序产生的必要条件。”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哲学美学促进了“原始积累”。露丝以慈善机构创办的孤儿院悬挂艺术品为例,这看似一项义举。然而,当我们了解到,悬挂这些艺术品只会增加其价值,而且这些孤儿院往往摇身一变成为艺术馆,例如伦敦著名的白教堂美术馆,这种活动的真实目的就昭然若揭了。
弗德曼认为人类的进步是非常偶然的
没有哪个行业是没有偏见的,古人类学家弗德曼·施伦克提醒我们,人们之所以很难接受新知识,是因为新知识往往与我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见相抵触,那些偏见甚至已经成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科学界面对压倒性的证据,却迟迟不肯接受非洲是人类的摇篮——从个古人类到智人都诞生在非洲——是这一点最好的例证。
一个同样顽固的偏见是,人类的进化是沿着一条笔直、有效和持续的道路前进的,直到进化成我们现在的高等形态。我们对进化的美好想象认为我们从树上跳下来就能直立行走,还能把树枝做成弓和箭。这样的概念在关于建筑起源的理论中很常见,特别是在已知最早的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筑文本中。他说,“古代的人,像野兽一样在树林、洞穴和小丛林中繁衍,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到某一天,稠密的树木受到风雨的冲击,它们的树枝相互摩擦而起火:目睹这一情况的人被吓坏了,纷纷逃离。当烈焰平息后,他们走到近前,身体从火的温暖中得到了安慰,他们向火中继续添加木头,以免火堆熄灭,他们把其他同伴召唤过来,用手势表达着火是多么有用。在这次聚会上,人们发出了不同声调的声音。通过每天不断的练习,他们赋予了这些偶然发出的音节约定俗成的含义。然后,指着最常用的东西,他们开始了对话,而这一切都因森林那场意外的大火而起。
一次起火,让大家聚在一起,开始了对话和群居,并且过上了定居生活。再加上与生俱来就高于其他物种的天赋的加持,人们可以昂首挺胸地直立行走,从容欣赏世间万物的瑰丽和日月星辰的光辉。他们还能用自己天生灵巧的双手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有人开始用树叶做屋顶,有人在山下挖洞,还有的甚至可以模仿燕子筑巢,用泥巴和瓦片建造屋舍。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观察其他物种巢穴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推理进行改进,他们建造了更好的住所。
弗德曼认为,我们的进步是非常偶然的(我们进化出的部分属性后来又被放弃了,但仍然在我们身体上保留下来),而且如果不是为气候改变所迫,我们也不会进化。如果森林的覆盖面积没有缩小,我们就不会离开树木;如果我们没有被迫涉足湿地,也不会直立行走。通常情况下,与其停留在当前的栖息地适应气候变化,我们更愿意迁移到气候宜人的,因此,最终我们离开了非洲大陆,前往世界其他地区。可以说,我们通过寻找新的居住地来解决问题,这甚至到了跨越星际的程度,正是我们习惯对这一事实的视而不见,才导致了我们共同家园的破坏。

《无用:人类最宝贵的工具?》内页插图。
1895年4月26日,也就是奥斯卡·王尔德因同性恋受审判的那个月,H.G.威尔斯(H. G. Wells)发表了他的著作《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书中时间旅行者来到了一个未来的世界——一个人类进化不受人类文明发展影响的世界。H.G.威尔斯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学生,赫胥黎是一位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因倡导进化论而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1893年,在19世纪最著名的科学讲座之一“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上,赫胥黎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进化并不取决于聪明、善良或其他美德,而取决于对环境的适应性,而这两者往往并不一致。在《时间机器》所描绘的世界中,时间旅行者看到未来的人类进化成为两种人:埃洛伊人(the Elois)和莫洛克人(theMorlocks)。埃洛伊人生活在地上,过着群居生活。他们身材矮小,精致美丽,像孩子一样四肢纤细,没有好奇心和纪律性。莫洛克人则面目狰狞,终年生活在地下,只在夜晚才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意识到埃洛伊人是被莫洛克人精心豢养的,莫洛克人把他们养肥了,然后再吃掉他们。莫洛克人设计了这个优雅的世界,让埃洛伊人没有兴趣发展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存技能。无用阶层在这反而被视为社会上层。埃布鲁·库尔巴克指出,“所有人都在发展自己在其特定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生存的技能。然而,一旦一个人迁移到另一个,有些技能就会变得完全过时”,换句话说,就是变得无用。这段话出自她的艺术作品《不常问的问题》(IFAQ),该作品为本书出版提供了很多灵感。我们在年发现了这个作品,当时我们正在思考、研究建筑和移民问题,它启发我们将这些想法与戈特弗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的观点融合起来,即墙面的装潢者或地毯的编织者在艺术史上占有最重要的一席之地。由于他的政治信仰,森佩尔本人曾被迫多次移民。迁徙是我们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移民的恐惧和反感同样古老,正因为如此,移民常常在学习定居民族的技能时遇到阻碍。编织篮子是一个例外,因为这符合迁徙的生活方式,不仅原材料是免费的,运输起来方便。
无用很少被理解,经常被滥用、被美化,
但依旧充满希望
在我们发现埃布鲁的作品时,曼海姆多功能厅,这座开创性的木制格子建筑、现代建筑的奇迹之一,正处于危险之中。荒废了40多年后,这个超薄轻质的木质网壳结构面临着被拆除的威胁,因为公众认为它没有用。米格尔·帕雷德斯·马尔多纳多认为,古典实用主义的定义是狭隘的,因为根据这一定义,“任何在形式组织和功能表现上找不到统一性的建筑作品都将被视为无用的。……因此,对建筑作品来说,似乎没有比无用更大的罪恶了。在当前生态危机和资源匮乏的大背景下则更是如此,无用往往意味着浪费。”其实,曼海姆多功能厅的空间并不是无用的,而是人们对此类空间缺乏或几乎没有经验。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对这样的空间没有什么经验,很少有遵从类似原则的建筑。而且,人们把它们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而不是探讨它们的潜在价值。

电影《博物馆时光》(2012)剧照。
曼海姆多功能厅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一个能源危机的时代。今天,在一个气候危机的时代,对此类的木质编织结构的进一步研究日益迫切:这种结构轻巧,用料经济,可以轻松移动和回收。为此,我们将与学生一起成立的工作室命名为“无用”,我们的个项目就是使用折叠的报纸发展编织技术,报纸是一天新闻的重要载体,而第二天就被视为无用之物。然后我们将其做成了编织容器的结构,其尺寸与人体相关,后来将其改进成最薄、最易折曲的胶合板。这些木质编织空间轻如鸿羽,以一种真正精致的、轻巧的方式包围着空间,即使有些经过一点修改就可以转化为空间,它们却骄傲地“无用”着。学生们说,一旦他们熟练掌握了编织技能,用到的材料真的少之又少,因此他们又给工作室起了一个名,少用(use-less)。
克斯汀·迈耶,一位在柏林、贝宁和塞内加尔工作的经济学家和活动家,将她保卫柏林坦佩尔霍夫公园的斗争的描述称为“无用之地——少占用地”(useless-land)。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她还写了一本柏林市宪法指南,而且将东西柏林的法律都纳入其中。尽管大多数允许公众发表意见的权利都被取消了,但有一项权利得以保留,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民公决权。掌握了这些知识后,她参加了保护柏林坦佩尔霍夫公园用地的人民运动,倡议其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加以保护。
这是一场特殊的草根运动,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当时柏林迫切需要建造更多的住房,而所有主要政党都支持对坦佩尔霍夫公园进行开发。但是,经过数千小时在街道、地铁和公园举着标语牌(当时还没有Facebook、Twitter或Instagram),与柏林公民一对一地直接对话,2014年5月25日,柏林人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将柏林坦佩尔霍夫旧机场保留下来。不仅暂时不会开发,法律还规定,不能将该场地列入任何长期规划。
当然,还是建造了一些基本设施,如浴室和维修小屋,有时会对一些区域进行修剪来保持草地的清洁,但除此之外,如何使用和享受这个场所,则完全由游客自己决定。事后看来,这一美妙空间得以维持的关键是把它的维护写进了法律。
多么希望英国住宅区的绿色空间当时也能如此啊。从1973年夏天开始,艺术家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 Clark,1968年毕业于建筑专业)发现纽约市正在拍卖一些不规则的小块土地,这些土地是分区和测量错误和异常结果,他买下了15个这样的“畸零地”(gutter spaces)。1975年,他出现在他的朋友詹姆·戴维多维奇(Jaime Davidovich)拍摄的一段中,当时他正借助地图来四处他的财产。这段记录了他如何测量那些地块并用粉笔标记,与邻居和路人的相遇,以及如何克服出入的困难。所有这些工作如果是为了有价值的地产再正常不过,但当用于“无用”的地产时就会变得很滑稽。

《无用:人类最宝贵的工具?》内页插图。
马塔·克拉克经常谈论这些地产,但当他死后,它们被遗忘了,而又重新归纽约市政府所有。他的遗孀后来找到了这些地块所有权证明的失效文件,并将其组装成拼贴画,这些拼贴画很快被艺术市场收购,并被命名为《现实财产:虚假房产,2497街区,42号地块》(Reality Properties:Fake Estates,Little Alley Block 2497,Lot42),其价值远远超过了房产本身。这件作品本身以及它所代表的地块被政府卖出又收回的事实,已经成为其他挑战资本主义的颠覆性工作的基石,即私人持有的不动产的内在价值。
同样,日本艺术家赤濑川原平(Genpei Akasegawa)在20世纪70年代发明了超艺术:(Hyperart:homasson)一词,当时他开始观察记录建筑和景观的某些部分,这些部分可能曾经有某个功能,但现在已经没有用了。为了符合超艺术的要求,研究对象必须失去其存在的原始理由,保持无用,并被精心维护。赤濑川用了大量精力来澄清艺术定义为无用的模糊性,他说:“……艺术实际上是一种功利性的东西,有一个目的。艺术的目的,……另一方面,超艺术,完全与艺术的目的无关。它甚至与日常事物通常具有的各种各样的目的无关。”
在这篇文章中,我用稀缺这个词来描述无用性,并不是要把它作为精英的主题,而是要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很少被理解,经常被滥用、被美化,但依旧充满希望。就像索尼娅·莱默的大型无用物品被人类的怀抱所征服一样。
本文选自《无用:人类最宝贵的工具?》,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 米歇尔·霍华德
摘编/何安安
编辑/张婷
校对/卢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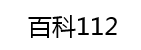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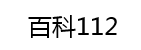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微乐龙江麻将有挂是真的吗”(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微乐龙江麻将有挂是真的吗”(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