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致邵祖平函。
为纪念郭沫若逝世一周年,《文艺报》1979年6月号发表郭沫若未刊书简多封。其中《致祖平》一通附以手迹,但未标年份,是这些未刊书简中最有意味的一封,值得考证与体味。
为便于解读,兹据手迹将全信迻录于下。
祖平先生:
二月二日给我的信,我拜读了。鲁迅先生确是不可及的。以他的年龄和所处的时代,象他那样跟着时代前进,一直站在最前头的人,实在少有。从发展的过程上来看,他自然也有些可訾议处。我的《庄子与鲁迅》,便是采取那样的角度来看的。鲁迅受过庄子的影响,但他在思想上已经超越了庄子。和韩非的思想更是立在两绝端的。只要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我觉得不算是失敬。
足下对我,评价过高,我自内省,实毫无成就。拿文学来说,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拿研究来说,根柢也不蹈实。特别在解放以后,觉得空虚得很。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著述研究也完全抛荒了,对着突飞猛进的时代,不免瞠然自 失。我倒很羡慕教学工作,时常能与青年接近,并能作育青年。立人立己,达人达己,两得其利。这事业是值得终身以之的。望足下不要轻视它。在四川住了十二年并不算长,重庆的偏僻正需要好的教师。
科学院无文学研究机构。丁玲所主持的研究院,以创作为主,年青人多,和先生的希望不符。我希望您仍然打起精神,为西南文化建设服务。学习马列主义,随处都可,不必北来。
此致
敬礼!
郭沫若
二月十七日
因落款仅书月日,故通信年份是个问题。信件涂抹甚多,但细察墨迹,抬头圈去的字当为“邵”,故祖平即邵祖平。这为推断年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邵祖平与郭沫若。(资料图/图)
《学衡》与鲁迅邵祖平(1898-1969),早年肄业于江西高等学堂,为章太炎高足。1922年任《学衡》杂志编辑,历任浙江大学、四川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重庆大学等高等学府教授,撰有《中国观人论》《国学导读》《词心笺评》《七绝诗论七绝诗话合编》《培风楼诗存》等著作,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有印记的知名人物。
郭沫若复信中有“在四川住了十二年”一语,显系由邵信获知。邵于1939年寓居四川,则邵信当写于1951年或1952年初。从“二月二日给我的信”一句推断,当写于1952年。邵氏的求助信虽无由得见,但因着邵氏当年行状,自可了解其缘由。
1951年10月21日,时任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邵祖平在本系纪念鲁迅座谈会上发言,对鲁迅的描述多有轻慢和失实之处。因着鲁迅《估〈学衡〉》一文的揭刺所产生的龃龉,多年来在课堂上,邵不但对鲁迅,而且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时有不满言论。但在纪念会这样的场合非议鲁迅,显然很不理智。邵的发言经重庆《新华日报》披露后,西南地区文化教育界对其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批判 ,最终以邵祖平公开书面检讨收场。作为中文系同人,吴宓在日记中的相关记载,透露出邵在遭到批判时的心境:“平已屈服,惟忧‘饭碗问题”;“今平既与熏(指系主任何剑熏,引者注)决裂,不得不速为下学期枝栖之计,实不能且不甘续任重大教授”。在这样的困境中,邵遂向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求助,希望能去中国科学院从事文学研究。
邵祖平的检讨,以《严格检讨我的错误,争取思想改造》为题,刊登在1952年1月中旬的重庆《新华日报》上,2月上旬《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当为郭沫若寓目。这也许是促成郭于当月中旬回复的一个因素。
私人通信多少可以直陈心事。郭沫若与邵祖平虽无交集,但行文的字里行间却流溢着少有的坦诚。
不难推测,邵信多半说到座谈会“非议”鲁迅一事。从复信的相关文辞看,以对当年鲁迅与郭沫若关系的了解,邵在信中吐露委屈或抱怨亦属正常,故有复信开头一段颇为精当的评论。1950年代中期,在编辑出版《沫若文集》时,有关人员要求删去《创造十年•发端》以维护鲁迅的形象。郭沫若“为了保留事实的真相”,坚持原貌。这正应了此信所说的“只要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我觉得不算是失敬”。
巧合的是,郭沫若复信当天,正是长达三万余字的《奴隶制时代》完稿之日。这一天,作者“把最近两年来所写出的有关中国古代的一些研究文字收辑成为这一个小集子,作为《十批判书》的补充”。这个“小集子”便是1949年之后出版的部学术著作《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在复信中情不自禁地吐露“著述研究也完全抛荒了”的隐衷,固然不乏自谦的成分,确实十分真实地表达出对于事功与学术的纠结。
两件事郭沫若是事功意识十分强烈的革命家。1926年6月,早已借《女神》而名满文坛的诗人,投笔从戎,开启北伐途次,谱写革命春秋。随后流亡日本十年(1928.2-1937.7),作为革命家虽无用武之地,但学术家的天赋异禀大显光彩,在古文字研究领域,成为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齐名的“四堂”之一。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出于民族大义,秘密返国,一度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日宣传大业。寓居陪都重庆期间(1939-1946),郭沫若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文工会1945年4月被解散),自谓“难出青木关一步”,却被推为“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恩来语),除创作《屈原》等6部历史剧,更在研究先秦文化领域写出《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著作。抗战胜利之后,郭沫若以无党派人士的“社会贤达”身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夏,离渝赴沪,与民盟诸公奔走于沪宁道上,呼吁“和平、民主、建国”。1947年春间,寓居沪上译竣《浮士德》第二部,恰在梁漱溟慨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亡”之后。
作为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在1949年10月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等三个要职,无疑对政治建树有着热烈的憧憬。然而,就在1952年2月,竟对一位平素并无过从的文化人士道出肺腑之语。
笔者以为,1951年所发生的两件事直接导致郭沫若作此想。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批判的锋芒,不但指向武训,更着重地指向宣传武训的人们。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
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公开的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做出适当的结论。
郭沫若虽然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从政,但事实上一直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追求而与中共领袖保持密切的关系。多年来的史学著作,一直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更重要的是,在新中国政权机构中,以副总理的要职具体和实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但是,在这场运动中,面对“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的指令,郭沫若所能选择的,就是迅速作公开的自我检讨。6月1日,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1天之后,郭沫若写出《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刊登在6月17日的《人民日报》:
我是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了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对于这样的人而加以称颂,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经过了这一次的讨论,我是受了很大的启发的。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随便发言,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随便替人题辞题字,这种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我已下定决心加以痛改。我诚恳地向读过《武训画传》的朋友们告罪。
仅仅过了两个月,郭沫若又一次公开检讨。事情的起因是陆定一看到中国科学院出版的马学良《撒尼彝语研究》,认为该书序言中对法国神甫邓明德的表述,存在立场问题,遂于7月 22日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及相关人员,强调:“为了加强中国科学院出版物的严肃性,提议考虑具体办法,予以补救。今后中国科学院的出版工作中,亦希能有具体办法,使此类政治性的错误不致发生。”郭沫若接信后深感问题的严重性,次日即致函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
莘田先生:
附上陆副主任(陆定一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信,阅后请掷还。关于本书具体补救办法,我拟了几条:(1)凡本院编译局、语言研究所赠送者全体收回;(2)通知商务印书馆立即暂行停售,发售以来已售多少,将确数见告;凡已售出之件,可能收回者亦一律收回 ;(3)该书必须将序文除掉,由马君改写,并将全体内容整饬一遍,再考虑继续出版。以上诸点,我将以回复陆副主任,至于中国科学院出版工作的一般具体办法,当另行商议 。
敬礼!
郭沫若 七月二十三日
据此,中科院迅即采取措施,处理已经出版的书籍,7月26日,还做出《关于的检讨》,承认“我们作为科学工作者的‘买办的思想’不仅未能肃清,反而在加以‘发展’,这确是值得我们深刻地检讨的”,强调此事“责任不限于作者马学良,科学院的各位负责人,科学院编译局及语言研究所的负责人,都有同样的责任。我们希望有关的负责同志们能深切诚恳地作一番自我检讨,这样来加强科学院出版工作的严肃性,并加强全中国科学出版事业的严肃性”。作为院长的郭沫若,自然要身体力行,《科学通报》1951年第10期刊登的《关于的检讨·结语》即出自其手:
《撒尼彝语研究》所犯的政治性的错误,首先是应该由我负责来自行检讨的。书在未印出之前,我没有亲自审查,在既印出之后我也没有细加核阅,这样的疏忽实在是万不应该。
大规模的武训批判事件发生之后,在中国科学院和编译局的检讨中,都提到武训批判一事。郭沫若本人则因曾经赞扬武训而先后两次在《人民日报》公开检讨。将郭沫若因武训问题所做的检讨和因《撒尼彝语研究》事件所做的检讨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在共和国文化事业的同时,郭沫若面临着怎样的思想压力。
由是之故,郭沫若慨叹“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这样的情状,在1954年届人代会由副总理移位副委员长(仍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更无从改观。1955年3月,郭沫若应邀参加中国科学院中共党组扩大会议,当着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陈毅的面,就加强科学院党的,说了这样一番话:“请中央派一位更高级的、真正有能力的同志担任院长职务,只有如此,才可以和政府有关各部有机联系,也可以统筹规划科学工作。我在这里不是说客气话,让我多写两篇文章比当两三年院长更有好处。请陈毅同志把这个意见向中央转达一下,不然,我见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是要提的。请中央不要把我当成统战对象看待,让我科学院的工作,确实值得考虑。”实系由衷之言。
管子研究这就有了1954年春撰写的《的研究》这样一篇长达近三万字的论文。写作的缘起在1953年11月接手的《管子集校》。(许维遹、闻一多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着手整理该书,原名《管子校释》,至1951年许氏去世,遗稿近四十万字。郭认为“许、闻旧稿仅属草创,严格言之,离成书阶段甚远”,故搁置甚久。)1954年9月下旬,郭沫若撰《叙录》。以下摘引,可知其学术追求:
整理工作费时凡十阅月,中因出国,曾中辍者两月,其余则大抵集中力量而为之。
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而文字复舛误歧出,如不加以整理,则此大批资料听其作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前人已费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释,但复散见群书,如不为摘要汇集,读者亦难周览。有见及此,故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
凡在整理过程中,对《管子》原书不能不反复通读,于诸家校释亦不能不反复校量,故于原文疑难处之通晓亦得时有弋获。因此使整理后之稿本增至一百三十万字以上,比许、闻原稿已增加三倍。
1955年11月,郭沫若写《校毕书后》:“本书之增订,计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接受许、闻初稿加以整理,至今二校校毕为止,费时整整二年。行有余力,大抵集中于此”。在陈述了种种“令人难以满意者”之后,以欣慰的心情告白:
本书如上所述,且有种种疵病,然于历来《管子》校勘工作,已为之作一初步总结。此一工作,于今后有志研究《管子》者,当不无裨补。此书之作,专为供研究者参考之用耳。使用此书时或不免有庞然淆杂之感,然如耐心读之,披沙可以拣金,较之自行渔猎,獭祭群书,省时撙力多多矣。
至余整理此书,亦复时有弋获。《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总汇,秦汉之际法家学说尤多汇集于此。……故欲研究秦汉之际之学说思想,《管子》实为一重要源泉。余久有意加以彻底研究,而文字奥衍,简篇淆乱,苦难理解。今得此机会,能将原书反复通读,凿通浑沌,已为此后研究奠定基础。二年之光阴,亦非纯然虚费也。
《的研究》正是集校过程中的研究成果。该文论证《侈靡篇》的制作年代为汉初“吕后专政时代”,论断其“基本上是一篇经济论文”,并论述其政法文教、军事国防之主张,分析作者的“阶级立场与思想背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探究侈靡学说衰颓的原因。以“余久有意加以彻底研究,而文字奥衍,简篇淆乱,苦难理解。今得此机会,能将原书反复通读,凿通浑沌,已为此后研究奠定基础”的学术自信,假以时日,《管子》研究或将与《十批判书》成并峙双峰。遗憾的是,《的研究》既是开篇,亦为终曲。《叙录》的结尾,算是留给后人的托付:
研究工作有如登山探险,披荆斩棘者纵尽全功,拾级登临者仍须自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知勤劳,焉能享受?关于《管子》全书之进一步研究,将尚有待。
由于时代的转换,郭沫若于“事功与学术”之纠结,终未释怀。
末了要说的是,这封涂抹甚多的信件,是否实寄,是个问题。得能公开发表,端赖郭沫若故居收藏,而非收信者家属或其他方面提供,当不为无故。
冯锡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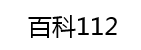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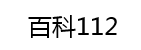 3分钟学会“么么哒麻将开挂方法”(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
3分钟学会“么么哒麻将开挂方法”(确实是有挂)-抖音官方" data-original="https://www.baike112.com/css/1.jpg" />